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怎么样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11/28 09:0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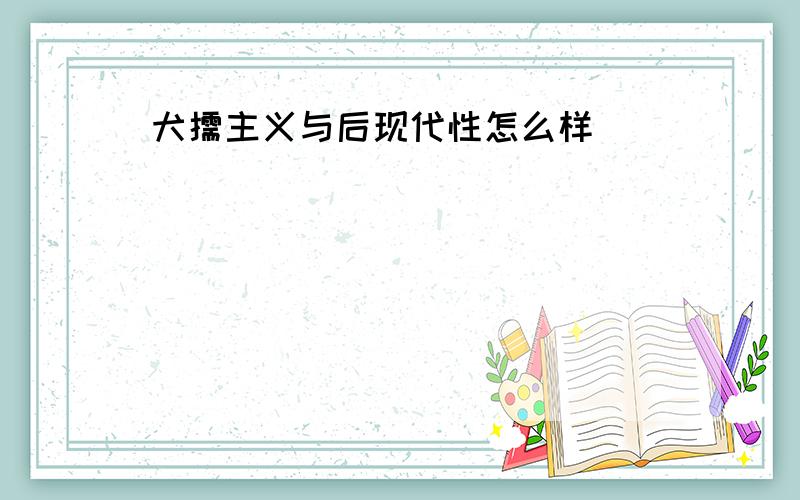
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怎么样
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怎么样
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怎么样
一弗兰克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的一个次要角色,当人们把目光聚焦于特雷莎、萨宾娜以及托马斯之间复杂纠葛的性爱时,倒可能忽视了他.这个热血青年不甘忍受单调乏味的现实环境,怀着狂热的理想,参战越南支持红色高棉.昆德拉写他的文字,充满了调侃与讥讽.对这部小说来说,弗兰克的形象不算重要;但对昆德拉来说,他对弗兰克的批判却道出了他的心声:一个人的愚蠢与媚俗或许比邪恶还要糟糕.弗兰克的形象颇具代表性,从司汤达的于连到福楼拜的弗里德里克,再到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反叛者、愤世嫉俗者,这一形象源远流长,连绵不绝.前年奥斯卡的获奖影片《末代独裁》(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不甘寂寞的苏格兰青年怀着美好的憧憬远赴非洲刚果,却差点死于非命.这样的人物无论在艺术作品还是在现实世界中都不在少数. 就个人品质而言,弗兰克他们无可指摘.他们充满热情,理想以及信念,不甘于一成不变的生活,单调乏味的世界.他们身上充满了青春的叛逆,激情与反抗.对于健康的个体而言,激情的生活是必要的.但他们纵有激情却不够智慧,盲目激情的后果令人忧心.即便他们在个体德性上如何真诚热忱,如何完美无缺,但无论如何他们身上缺一样东西——“政治感”.尽管这是我个人杜撰的一个词汇,但它的“所指”是客观存在的.无论过去还是今天,它都是萦绕在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棘手的命题,尽管这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 生活在今天的时代,人们需要有必要的政治感.尽管没必要像米歇尔61福柯那样虚张声势说“一切都是政治”,但我们却也得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看似“去政治化”的时代其实处处隐藏着政治危机.按照日本学者加藤节(TaKashi Kato)的看法,当今社会政治对人的控制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变本加厉.随着现代制度的日益健全,政治权力能够加以统治和支配的人群范围已经无限扩大;同时,政治权力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此外,政治的影响力正不断地扩展到政治以外的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从今年奥运会的情况看,无论是抵制还是彰显国威,体育都摆脱不了被政治化的命运.因此今天“我们不能脱离政治,退隐到私人生活中去,也无法想象自己被统治的方式不会对我们的个人幸福产生巨大的影响.”(David Miller) 一方面是政治控制与权力渗透的无所不在,潜移默化,但另一方面却是被控制对象的麻木与冷淡.令人诧异的是,人们的政治感反而随着政治控制的加强不进反退,心甘情愿地将自身的命运托付于政治权力.一般民众以排斥和远离政治的方式制造了一种洁身自好的假象,却不明白不闻政治的后果正中了权力野心的下怀;许多知识分子貌似热衷政治,但事实上却从不愿为理解政治付出一丝一毫的努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因为趣味而拥戴某种政治,他们不关心现实的政治却只爱自我浪漫化的政治;他们也会激烈地抨击体制,反抗权力,但很多时候他们的批评有虚张声势之嫌,他们对体制的挑战并没有对其造成致命的打击,反倒是他们的批判姿态成就了他们个人在体制中的地位.无论从一般个人还是知识精英,政治判断力的下降已经显而易见,而政治感的缺失将严重影响到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品质与幸福.因此,政治感是如何的重要,在政治冷淡的当代社会,重建个体的政治感完全有必要提上日程. 二政治感的缺失是普遍的,本文把更多的聚焦置于知识精英.一方面,知识分子在知识与思维方面的优势本该使他们具有更明智的判断力;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观点与判断也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舆论.因此从根本上说,政治感还是知识精英的问题,一般大众不关注政治,也没有能力关注政治,但这并不妨碍知识分子的观点,尤其是那些糊里糊涂的政治见解抵达大众的潜意识,它的蛊惑性和煽动性不容小视.卡尔61波普尔曾悲怆地感叹知识分子与二十世纪的绝大多数罪恶脱不了干系,而当代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也彻底祛除了知识分子头顶神圣的道德光环. 政治感是何时成为一个问题的呢?我们似乎很难在历史中找到一个确定的坐标.粗浅地说,它凸显于从古典公民人格向现代个体人格的转型过程中,而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则是最具标志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基本奠定了今天生活中的日常人格.思想家卡尔61施密特与以赛亚61伯林从迥然不同的立场出发批判浪漫主义,却在对浪漫派政治感缺失的认识上意外达成共识.在《政治的浪漫派》中,施密特猛烈地抨击浪漫派的政治观,认为这是一种无根基性的任凭情绪摇摆而左右的东西.在其哲学中,政治决断至关重要,它代表了个体对政治的道德感与责任感,但对于浪漫派而言,他“除了体验以及用感人的方式阐释自己的体验外,不想做任何事情”.在深入分析浪漫派主体的过程中,施密特进而发现,浪漫派其实并不关心真正的现实政治,而是将政治随心所欲地诗化;浪漫的个体绝不是通过审慎合理地思考而做出政治判断的,他对某种政治的推崇完全是因为这种政治突然符合了他一时的心情与趣味.因此,随着他个人心情的变化与趣味的转移,他的政治观点也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从未有过“严肃的政治关切”. 与施密特对浪漫主义的痛斥相比,伯林对其倒是满怀同情.他一再肯定浪漫主义所开启的多元价值观.在那篇酣畅淋漓的讲演稿《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施密特的“机缘主体”在伯林那变成了“真诚的主体”,并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最高的价值是诸如正直、真诚,随时准备为某种内心理想献身,为某种值得牺牲一切,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奉献一个人的所有.”在这套全新的价值标准下,个体的内在动机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只要你是真诚的,无论你信仰什么,做什么事情,造成什么后果,都是可以得到理解的.因此,人们不再关注具体政治见解上的大是大非,而把更多的目光聚焦于“真诚的自我”.因为卢梭的真诚,人们可以原谅他的诸多过错,人格上的透明与纯粹似乎可以赦免行动上的罪恶;出于同样的理由,人们似乎也可以因为希特勒的真诚而原谅纳粹主义的罪恶.当真诚走向了狂热,自我走向了极端,它“破坏宽容的日常生活,破坏世俗趣味,破坏常识,破坏人们平静的娱乐消遣”.在此,伯林也不得不说“有些浪漫主义走得太远了.” 伯林与施密特表面上纠缠于历史,实质意指当下,人们在浪漫主义时代就基本形成了今天现实中的现代人格.因此,他们对浪漫派政治观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后来的历史.他们对浪漫主义政治观的批判,同样回应了当今世界个体政治感的问题.无论是之后的存在主义、批判理论,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虽然提出的理论各有千秋,但在处理政治问题上的方式却显得大同小异.“真实”代替了“真诚”成为了后期哲学的主导力量,从而将主体的情感引向更为隐秘的欲望.“他人即地狱”的萨特哲学宣告了“反政治”政治的诞生,后现代主义更是将此推向激进. “对政治家的普遍怀疑,对政治制度大范围地丧失信心,对神秘世界观的兴趣全面复活,以‘非人性化’和‘极权化’为理由持续怀疑启蒙话语的现代性与合理性,充满怀旧感地、甚至是以游戏的姿态投身于再度发明或者再度发现‘失落的纯真’的活动之中.”(提摩太61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第11页)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还在乌托邦的理想层面为真实的政治保留了空间,后者却在意识形态解构的大旗下,彻底打消了对理想政治的憧憬.如果在前者看来,自由、民主、平等还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至高价值的话,那么在后者眼里,这些价值本身就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欺骗,是不值得顶礼膜拜的. 不过,无论是乌托邦政治还是虚无主义政治,它们在本质上都试图逃离现实的政治领域.在个体解放的名义下,一切外在的现实政治都是枷锁和樊笼.随心所欲地谈论政治,不加思考地愤世嫉俗.在此意义上,他们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感觉”,他们津津乐道的仅仅是“感觉的政治”.勒庞的《乌合之众》提醒人们,未经审慎观察和理智思考,“感觉的政治”遗害无穷,二十世纪的人类灾难更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三因此,从感觉的政治走向政治的感觉刻不容缓.政治感并非先天的自然感受,而是来自于后天的文化构建.因此,构建有效的政治感的前提在于处理好两个层面的关系.其一是灵魂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关系;其二是现实领域与理想领域的关系.前者强调个体在理解政治过程中所应具有的现实感;后者则触及个体对政治的理想诉求.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政治有高超的洞见,他认为灵魂领域与政治领域绝不能混为一谈.一方面,灵魂的满足与否不能成为衡量政治的唯一标尺;另一方面,政治也不应当试图“关怀灵魂”.但从现代到后现代人类文化的发展态势来看,两个领域之间的边界愈渐模糊,甚至不复存在.政治开始被灵魂的形而上学接管,它似乎暗示了这样一个结论:只要达到灵魂的“本真”与“纯粹”,一切政治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从阿多诺、霍克海默到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对“本真性”的角逐似乎替代了现实政治领域的小修小补. 这个结论显然下的过于简单仓促.“本真”个体的政治判断力在阿伦特那里即遭质疑,艾希曼的道德真诚与崇高并不能确保他在政治选择上的愚蠢和平庸;而海德格尔高深哲学与低俗政治理念之间的断裂,更让人心生疑惑.甚多的事实表明,个体灵魂的纯洁与明智的政治选择绝没有直接联系,洞悉存在奥秘跟捍卫社会正义也绝非一脉相承.因此,把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灾难全都归因灵魂的异化,理性的滥用,而不去寻找具体特殊的缘由,在根本上只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正如尼采所言:“觉得各处都很相像,所有事物都是一个模样,这是视力变弱的一个迹象.”同时,这种思考方式在道德上也显得形迹可疑,在根本上放弃了政治责任.它是“以内在抵抗的名义,从被围困的政治世界中的撤出”,当代的犬儒主义由此粉墨登场. 以“本真性”的理由,这种弥漫于当代的犬儒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刻意夸大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它似乎在暗示,政治行动必然损害个体的本真,若要免于政治的异化,除非是把政治上升到本真性的高度去.在《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中,提摩太61贝维斯就认为: “后现代政治是一种本真拜物教的操作方式,形而上学的真理在其中绝望地得到了殷勤的关爱,而非简单地被弃之不顾.”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犬儒因缺乏本真而放弃政见.表面上愤世嫉俗,实质上是政治能力的羸弱.以萨尔曼61拉什迪事件为例,拉塞尔61雅各比论证了这个时代稀薄的政治感.“假如说拉什迪事件是一场考试,那么许多西方知识分子都失败了.”一桩关乎是非曲直的事件,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幌子下变得扑朔迷离,为了所谓的“客观”与“本真”,知识分子竟放弃正义的立场而沦为相对主义者,“问题不在于知识分子站在了错误的一方,而在于他们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一方.” 因此,灵魂有灵魂的问题,政治也有政治的问题,我们不能单从灵魂出发思考政治,或者单从政治出发思考灵魂,应更多地从政治现实本身来思考政治:政治就是这样一种介于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事物,它既不精确又不可缺少. 当然,拒绝把政治纳入灵魂的形而上学,强调政治的现实性,并不意味着灵魂就不能对政治提要求,或者说,政治就不该有理想的维度.用乌托邦实践来规范政治是一回事,用理想来引导政治又是另一回事.雅各比批判当代政治文化的鼠目寸光,政治乌托邦的罪恶不改牵连到理想主义文化的生长.后现代主义借反极权主义,反政治乌托邦之虚,却行犬儒主义之实.这种文化的弥漫,消解了希望与信仰,制约了想象与创造,人类的政治将陷入虚无主义的徘徊状态,“生活缩短为直接选择的运算;未来则瓦解成现在.”因此,即便在反乌托邦时代,我们也要谈政治理想.“我们既要对脚下的东西保持警惕,但是对于地平线上的东西同样要有所警惕.真正的乌托邦理想并不应该蔑视日常生活.”理想是我们导航的星斗,凭借星斗来指引航向,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航船开到星斗上去. 那么,在政治乌托邦之后的时代,真正的乌托邦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它又何以可能呢?灵魂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提示我们,个体理想虽关联于政治理想,但绝不能取代政治理想.政治理想不是一个人的导航星,而是众人的导航星.谁若主张靠一颗星而不是另一颗星导航,他就必须证明唯有那一颗星能指引我们实现所有人的奋斗目标.在这个时候,个体之间需要倾听、协商、理解以及做必要的妥协,政治理想需要激情和勇气,更需要审慎的现实感与责任感.因为正是现实本身为我们确立了政治的理想,确立了奋斗的方向和前进的速度. 就这样,政治感处于一种灵魂与现实,理想与必然的关系之间,在狂热的年代,它表现为冷静;在虚无的年代,它倒会显露热情的火花.作为个体,你完全有理由任性、叛逆、奔放、流浪、虚无,但作为政治共同体,却无法像个体那样承受因任性而付出的代价,因为它必须为每一个鲜活而卑微的个体幸福负责.政治感不同于自然激情,它将以低调的理想主义和审慎的现实感,在捍卫文明的果实过程中彰显人类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