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人教版课文《装在套子里的人》文章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7/11 04:3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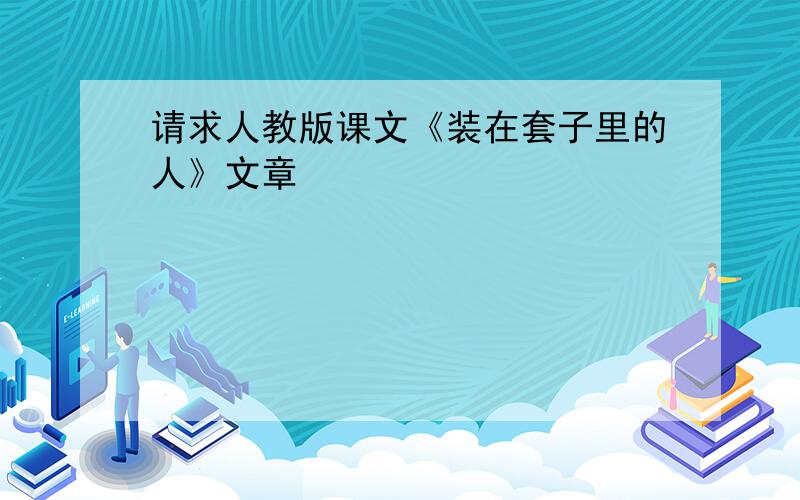
请求人教版课文《装在套子里的人》文章
请求人教版课文《装在套子里的人》文章
请求人教版课文《装在套子里的人》文章
《装在套子里的人》 契诃夫
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也真怪,即使在最睛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这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的东西;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现实生活.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上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他就觉得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好,这就行了.但是他觉着在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许里面,老是包藏着使人怀疑的成分,包藏着隐隐约约、还没充分说出来的成分.每逢经过当局批准,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
凡是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闷闷不乐.要是他的一个同事到教堂参加祈祷式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说是中学的学生闹出了乱子,他总是心慌得很,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那种多疑,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出气.他说什么不管男子中学里也好,女子中学里也好,年轻人都不安分,教室里闹闹吵吵——唉,只求这咱事别传到当局的耳朵里去才好,只求不出什么乱子才好.他认为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那才妥当.您猜怎么着?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和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眼镜,降服了我们,我们只好让步,减低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到后来把他俩开除了事.我们教师们都怕他.信不信由您.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可是这个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小人物,却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着他辖制呢!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礼拜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听见;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也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么事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别里科夫眼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他的卧室挺小,活像一只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着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叫,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他通宵做恶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并排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
可是,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差点结了婚.有一个新史地教员,一个原籍乌克兰,名叫密哈益·沙维奇·柯瓦连科的人,派到我们学校里来了.他是带着他姐姐华连卡一起来的.后来,由于校长太太的尽力撮合,华连卡开始对我们的别里科夫明白地表示好感了.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怂恿总要起很大的作用的.人人——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们——开始对向别里科夫游说:他应当结婚.况且,华连卡长得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产;尤其要紧的,她是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
定结婚了.
但是华连卡的弟弟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讨厌他.
现在,你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张漫画,画着别里科夫打了雨伞,穿了雨鞋,卷起裤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华连卡;下面缀着一个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您知道,那神态画得像极了.那位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教师们、神学校的教师们、衙门里的官儿,全接到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一份.这幅漫画弄得他难堪极了.
我们一块儿走出了宿舍;那天是五月一日,礼拜天,学生和教师事先约定在学校里会齐,然后一块走到城郊的一个小林子里去.我们动身了,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下竟有这么歹毒的坏人!”他说,他的嘴唇发抖了.
我甚至可怜他了.我们走啊走的,忽然间,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他的后面,华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来了.涨红了脸,筋疲力尽,可是快活,兴高采烈 .
“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多可爱的天气!多可爱,可爱得要命!”.
他俩走远,不见了.别里科夫脸色从发青到发白.他站住,瞧着我.
“这是怎么回事?或者,也许我的眼睛骗了我?难道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问,“让他们尽管骑他们的自行车,快快活活地玩一阵好了.”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起来,看见我平心静气,觉得奇怪,“您在说什么呀?”
他似乎心里乱得很,不肯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心神不地搓手,打哆嗦;从他的脸色分明看得出来他病了.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在他还是生平第一回呢.他没吃午饭.将近傍晚,他穿得暖暖和和的,到柯瓦连科家里去了.华连卡不在家,就只碰到她弟弟.
“请坐!”柯瓦连科冷冷地说,皱起眉头.别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了:
“我上您这儿来,是为要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我烦恼得很,烦恼得很.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画了一张荒唐的漫画,画的是我和另一个跟您和我都有密切关系的人.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事没一点关系.……我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该得到这样的讥诮——刚好相反,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
柯瓦连科坐在那儿生闷气,一句话也不说.别里科夫等了一忽儿,然后压低喉咙,用悲凉的声调接着说:“另外我有件事情要跟您谈一谈.我在这儿做了多年的事,您最近才来;既然我是一个比您年纪大的同事,我就认为我有责任给您进一个忠告.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者来说,是绝对不合宜的!”
“怎么见得?”柯瓦连科问.“难道这还用解释吗,密哈益·沙维奇,难道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倒过来,用脑袋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件事,那就做不得.昨天我吓坏了!我一看见您的姐姐,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一位小姐,或者一个姑娘,却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您到底要怎么样?”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密哈益·沙维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马马虎虎,唉,这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衬衫出门,人家经常看见您在大街上拿着书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说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么?”
“讲到我姐姐和我骑自行车,这可不干别人的事.”柯瓦连科涨红了脸说,“谁要来管我的私事,就叫他滚!”
别里科夫脸色苍白,站起来.“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面前谈到上司的时候不要这样说话;您对上司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对上司说了什么不好的话?”柯瓦连科问,生气地瞧着他.“请您躲开我.我是正大光明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不喜欢那些背地里进谗言的人.”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脸上带着恐怖的神情.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别人对他说这么不客气的话.
“随您怎么说,都由您好了.”他一面走出门道,到楼梯口去,一面说,“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了,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他?去,尽管报告去吧!”
柯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前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摸鼻子,看了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华连卡回来了,带着两女士.她们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何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说不定又会有一张漫画,到头来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等到他站起来,华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着:
“哈哈哈!”
这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结束了预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没听见华连卡说什么话,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一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华连卡的照片;然后他上了床,从此再也没起过床.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
我们要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忧郁和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自由的时候,才经历过.
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家.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动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装在套子里的人
契诃夫
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也真怪,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那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
全部展开
装在套子里的人
契诃夫
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也真怪,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那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这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剌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现实生活。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他就觉得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好,这就行了。但是他觉着在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许里面老是包藏着使人怀疑的成分,包藏着隐隐约约、还没充分说出来的成分。每逢经过当局批准,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
“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
凡是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闷闷不乐。要是他的一个同事到教堂参加祈祷式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说是中学的学生闹出了乱子,他总是心慌得很,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那种多疑,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出气。他说什么不管男子中学里也好,女子中学里也好,年轻人都不安分,教室里闹闹吵吵——唉,只求这种事别传到当局的耳朵里去才好,只求不出什么乱子才好。他认为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那才妥当。您猜怎么着?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和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眼镜,降服了我们,我们只好让步,减低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到后来把他俩开除了事。我们教师们都怕他。信不信由您。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可是这个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小人物,却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着他辖制呢!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礼拜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昕见;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也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么事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别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他的卧室挺小,活像一只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着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叫,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他通宵做噩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并排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
可是,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差点结了婚。有一个新的史地教员,一个原籍乌克兰,名叫密哈益·沙维奇·柯瓦连科的人,派到我们学校里来了。他是带着他姐姐华连卡一起来的。后来,由于校长太太的尽力撮合,华连卡开始对我们的别里科夫明白地表示好感了。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怂恿总要起很大的作用的。人人——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们——开始向别里科夫游说:他应当结婚。况且,华连卡长得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产;尤其要紧的,她是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结婚了。
但是华连卡的弟弟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二天起,就讨厌他。
现在,您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张漫画,画着别里科夫打了雨伞,穿了雨鞋,卷起裤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华连卡;下面缀着一个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您知道,那神态画得像极了。那位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教师们、神学校的教师们、衙门里的官儿,全接到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一份。这幅漫画弄得他难堪极了。
我们一块儿走出了宿舍;那天是五月一日,礼拜天,学生和教师事先约定在学校里会齐,然后一块儿走到城郊的一个小林子里去。我们动身了,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下竟有这么歹毒的坏人!”他说,他的嘴唇发抖了。
我甚至可怜他了。我们走啊走的,忽然间,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他的后面,华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来了,涨红了脸,筋疲力尽,可是快活,兴高采烈。
“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多可爱的天气!多可爱,可爱得要命!”
他俩走远,不见了。别里科夫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他站住,瞧着我。……
“这是怎么回事?或者,也许我的眼睛骗了我?难道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问“让他们尽管骑他们的自行车,快快活活地玩一阵好了。”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起来,看见我平心静气,觉得奇怪,“您在说什么呀?”
他似乎心里乱得很,不肯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心神不定地搓手,打哆嗦;从他的脸色分明看得出来他病了。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在他还是生平第一回呢。他没吃午饭。将近傍晚,他穿得暖暖和和的,到柯瓦连科家里去了。华连卡不在家,就只碰到她弟弟。
“请坐!”柯瓦连科冷冷地说,皱起眉头。别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了:
“我上您这儿来,是为要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我烦恼得很,烦恼得很。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画了一张荒唐的漫画,画的是我和另一个跟您和我都有密切关系的人。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事没一点关系。……我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该得到这样的讥诮——刚好相反,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
柯瓦连科坐在那儿生闷气,一句话也不说。别里科夫等了一忽儿,然后压低喉咙,用悲凉的声调接着说:
“另外我有件事情要跟您谈一谈。我在这儿做了多年的事,您最近才来;既然我是一个比您年纪大的同事,我就认为我有责任给您进一个忠告。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者来说,是绝对不合宜的!”
“怎么见得?”柯瓦连科问。
“难道这还用解释吗,密哈益·沙维奇?难道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倒过来,用脑袋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 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昨天我吓坏了!我一看见您的姐姐, 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一位小姐,或者一个姑娘,却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您到底要怎么样?”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密哈益·沙维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马马虎虎,唉,这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衬衫出门,人家经常看见您在大街上拿着书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听说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吗?”
“讲到我姐姐和我骑自行车,这可不干别人的事。”柯瓦连科涨红了脸说,“谁要来管我的私事,就叫他滚!”
别里科夫脸色苍白,站起来。
“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面前谈到上司的时候不要这样说话;您对上司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对上司说了什么不好的话?”柯瓦连科问,生气地瞧着他。“请您躲开我。我是正大光明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不喜欢那些背地里进谗言的人。”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脸上带着恐怖的神情。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别人对他说这么不客气的话。
“随您怎么说,都由您好了。”他一面走出门道,到楼梯口去,一面说,“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了,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苦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他?去,尽管报告去吧!”
柯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了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华连卡回来了,带着两位女士。她们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何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说不定又会有一张漫画,到头来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等到他站起来,华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着:
“哈哈哈!”
这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
结束了预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没听见华连卡说什么话,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一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华连卡的照片;然后他上了床,从此再也没起过床。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
我们要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忧郁和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自由的时候,才经历过。
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家。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