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11/06 05:5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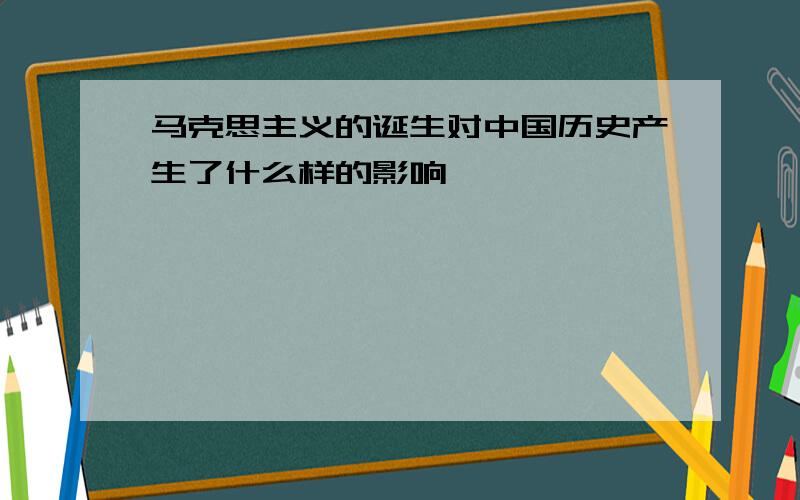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x0d现在有许多人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不提马克思主义,提到马克思主义就觉得很荒唐,觉得很可笑.所以我要在这里谈谈,咱也不说深了,就通俗地说说.\x0d万事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古人说在毒蛇出没的地方,五步之内就一定有克制它的植物或者其它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和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工人分不开的.它的产生就是要使工人摆脱这种被剥削被压迫的处境.有的人可能不相信那时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工人,我举个简单例子,大家看过卓别林的电影没有,那里面资本家为了节约工人吃饭的时间,专门发明了喂饭机!当然,艺术有它夸张的成份在内,但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资本家是怎么剥削工人的.\x0d所以马克思主义一出现,立刻就被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武器,进行了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顶峰时爆发的.所以不可避免地,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不仅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甚至渗入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有组织的罢工等运动风起云涌.\x0d反毛反马者们,你们不是也在说美国的工会势力很大吗?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得不重视工人的权利,不得不承认工会的权力!\x0d反毛反马者们,你们不是也说美国、德国的社会保障好吗?福利高吗?那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得不重视这些地方!\x0d因此,我们现在享有的权益,世界的和平,可说是托马克思之福!\x0d虽然马克思主义现在没有人提了,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已所剩无几,但是马克思的影响依然存在,无论在哪里都有它的影子.虽然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缺陷,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因这样那样的偏差而暂时失败了,但是马克思主义总有一天会重新光芒四射的.这不是我痴人说梦,而是由资产阶级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它要剥削,要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本.虽然它现在很温和,虽然它现在很克制,但是一旦当人民越来越忘却马克思主义,它越来越猖狂时,那么无产阶级必然起来,起来时比上一次更成熟,它的好日子就结束了.\x0d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由于种种原因向来被疏忽和延宕了——如果说它在哲学上未被坚决而内在巩固地指证出来,那么它在实际境况中也就这样那样地被一般观念悬置或遗忘了.然而,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如此紧迫地要求理解这种当代意义,要求给予这种当代性以深刻的阐述和精详的论证.我们的这篇短论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而只是试图在哲学方面提示出问题的若干要点罢了.\x0d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一马克思哲学是真正的当代哲学.该判断在最为通常的划界的要求上是指:它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近代哲学.这一点难道说有什么疑问吗?必须承认,存在着疑问.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如果说上述判断在一方面得到最高度肯定的话,那么它在另一方面恰恰是受到最坚决的否定性抵制的.倘若事情是仅仅牵涉到所谓“学派阵营”的划分,那问题倒真是太简单了.然而实际情形是:对于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那种高度肯定往往只是以最抽象和最空疏的辞令表现出来,它在哲学的基础方面根本没有成为内在巩固的东西;这样一来,即便我们不必去谈论“授人以柄”如何的不明智,重要的问题却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被遮蔽起来了.\x0d我们在这里无需去学究式地探讨哲学之近代性和当代性的划界.在哲学上,问题的要害是“理性形而上学”.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黑格尔理解为近代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伟大综合者和完成者,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权宜地把这界限指派给黑格尔哲学.毫无疑问,这条界限根本不是年代顺序的定义,它所涉及的是任何一种哲学的实质及其权衡.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马克思完全正当地把费尔巴哈哲学的结果了解为黑格尔性质的一样,萨特亦不无理由地规定基尔凯郭尔学说在归宿方面乃为黑格尔哲学的一支.这条界限的意义纯全是由现实生活的真正历史性所开启的,正像它在哲学上是通过当代哲学的整个运动而得以呈现的.如果说我们在这里不必去顾及“哲学史教程”的那种疏阔的全面性和公正性,而仅只关心提示问题所在的那个核心,那么,关于当代哲学运动——它的枢轴与过程——我们只需提到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名字就够了.\x0d然而,真正批判地意识到这条界限并对其意义作出决定性开启的第一人乃是马克思.不幸的是,这个具有最关重要的哲学革命事件——它的划时代的功绩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却逐渐被遗忘了.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一“革命”及其功绩和意义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谈论,不,情形恰好相反.但重要的现象实情在于,当一件事情越是进入到“闲谈”之中,越是被抽象地和空疏地吹嘘着的时候,人们对其真实意义的遗忘就越是深切.千万不要纯全主观地来理解这种“不幸的遗忘”,好像它本来可以借助于聪明而被避免似的.事情完全不是如此.毋宁说,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讲,这种遗忘倒更像是它的“命运”;甚或可以在一种比拟的意义上说,宛如是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狡狯”.\x0d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实际地主宰着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权时,上述“遗忘”不仅在普遍地发生,而且也在不断地加剧.此一事件的典型症候便是马克思哲学愈益被沉没到“近代性”的基本观念之中,并且通过这些观念而分裂了马克思哲学的真正基础.这种分裂情况,首先可以初步地(或许也是较为表面地)在马克思哲学的“实证化”过程中被揭示出来.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作为整体,不遗余力地——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推进着这一“实证化”过程;换言之,他们共同制造着马克思哲学作为“知性科学”和“实证科学”的神话.这个神话的口号便是“经济决定论”;然而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于,无论是学派内部还是外部对这个口号的批评、攻击和修正都不曾真正瓦解这个神话,相反却在加强和巩固这个神话(注:参见拙著《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一书“导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不难看出,这个神话的秘密就是在哲学上向“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大踏步地倒退.普列汉诺夫这位第二国际最出色的理论家,对“经济决定论”发表了那么多的批评、调整和补充意见;但是,临到他遭遇真正的哲学问题,例如,当他感觉到“生产力”的客观性仍不充分因而必须使之进一步还原为“地理环境”的时候,当他把马克思的意识理论同丹纳的艺术哲学公式相比附的时候,当他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天真断言“哲学问题”有朝一日可以用数理计算来解决的时候,我们无疑是看到了一种只有在孔德主义那里才能见着的极端形式的实证主义.\x0d我们当然可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但这种谈论决不是无条件的——它的条件就是使其根本的哲学基础得到真正的因而也是历史的阐明.因此,第二国际理论家所实行的那种“实证化”恰恰就是使这一哲学基础停留于晦暗之中;不仅如此,他还在这一过程中实际地偷换了自身的哲学基础,并且沉溺于“知性科学”立足其上的那些理智形而上学前提.这一事实不过表明:马克思哲学的真实基础和当代意义对于他们来说乃是蔽而不明的.\x0d如果马克思的哲学——特别是作为其根本“纲领”的共产主义——果真仅只是一种实证科学或知性科学的话,那么,立足于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人们当然就有理由来议论此种科学的“可证伪性”,并且声称根据了或多或少的“经验反证据”已经决定性地证伪了共产主义.这样的议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大概自90年代以来尤其热烈.然而,当这种实证科学之勤勉而坚韧的守门人拉卡托斯根据了精致的可证伪性而坚拒马克思主义进入科学殿堂时(注:参见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他实在只是在同风车作战.这里无需去谈论他的“科学”概念及其哲学根据,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或共产主义从来就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实证科学或知性科学.\x0d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或共产主义毕竟不可能一无遗漏地被还原为上述的知性科学,那以,应当如何去理解和说明它的“溢出部分”或“批判方面”呢?也许初看起来多少有点出人意外,这样的部分或方面被一再地解释为“宗教因素”——无论是把它们同某种实际的宗教相比附,还是把它们当成作为“理念目标”的理想和信仰,或者干脆是抽象意志冲动的对象.事实上,这种情形不足为怪,因为当马克思的哲学-共产主义被当作知性科学来规定的时候,它的真实基础实际上已经从中间“爆裂”了,而分裂开来的另一端便自然落入了“宗教因素”之中;正像在近代世界之完成了的文化形式中,宗教关怀矗立在知性科学的对面并作为它的真正补充(康德哲学).如此这般地把马克思哲学淹没到近代性观念的强制之中并从而肢解其基础的做法,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得到了典型的表现:正像他在一方面把唯物史观作为经验实证科学来赞赏一样,他在另一方面把共产主义完全拉进了基督教的观念世界,并且开列出一张详尽的对照表,以便使这两者的细节获得一一对应的关系(注: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47-448页.).我们同样注意到,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谈到了马克思主张要认识并承认“合人性的人”,并根据这一点而使之同基督徒从对神性的划界中来规定人性的看法相比照(注: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64页.).虽然海氏在这里完完全全地曲解了马克思,但他却正确地揭示了这样一种本质联系,即奠基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与基督教的救世框架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灵魂得救的教义完全可以不同理智形而上学的知性科学相冲突,而是构成它的必要补充.二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也就是它的真正的历史性,而这种当代性之被历史地遮蔽,其根由正在于现实生活本身的当代意义尚未得到充分的自我肯定;因此,这一哲学的当代意义也必定只能再一次历史地生成,亦即历史地被再度揭示和重新发现.伽达默尔在其写于1962年的一篇论文中说,20世纪的先驱者们曾团结一致地反叛19世纪的精神,在他们那里,“19世纪”这个术语意味着“滥用,代表着不真实、没有风格和没有趣味——它是粗糙的唯物主义和空洞的文化哀婉的组合.”(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然而,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20世纪并没有真正结束这种状况,所谓“后工业文明”从根本上来说乃是“工业文明”的精致化和进一步发展.这样一种世纪性目标的未被实现使一些人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而这种失落感在某些敏感的思想家那里被尖锐地体会到并被申说出来了.只要读一读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那部著名的对话录——它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叫做《展望二十一世纪》,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在试图对下个世纪有所期待的地方,他们以多么空疏的精神性原理同庞大黝暗的物化世界相抗衡,又以多么伤感和绝望的浪漫主义批判来抗议那种已远离了思想生命的理智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x0d20世纪最有价值的哲学努力虽然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些遥远了,但它决没有也不会被白白地经历.如果说黑格尔以复辟17世纪形而上学的方式对主观精神所作的批判乃是留给本世纪哲学思想的伟大遗产,那么,本世纪对这一批判的继承甚至可以说在哲学上极富成果地袭击了理性形而上学本身.当德国唯心主义的“同一哲学”在消除一切形而上学的二元论预设方面的努力被证明为虚假的时候,这种哲学的天真假设——根据伽达默尔的概括,它们是(1)断言的天真;(2)反思的天真;(3)概念的天真——乃被决定性地揭穿了(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127页.).因此,在哲学范围内,现在是理性形而上学本身(不是它的某些结论或方法,而是其基本的前提和立足点)从根基上动摇了.确实,海德格尔完全有理由根据已然达致的成果而把继续坚执其天真的形而上学称之为真正的哲学“丑闻”,把继续在此种前提上提出的问题——例如,追问孤立绝缘的主体如何达到对所谓“外部世界”的知识——看成是荒谬的和陈腐的.然而,如果说理性形而上学的这种根基动摇并未立即导致其决定性的崩溃,那么这是因为,并且仅仅是因为“最终崩溃”的根由决不局限于哲学的范围之内.\x0d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不仅应当而且必然得以呈现.如果说只有在当代哲学已然打开了的那个语境中才能使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得到充分估价的话,那么,下述事实乃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对全部旧哲学的批判可以被归结为对黑格尔的批判,并且因为如此马克思的这一批判不仅是对黑格尔的哲学的批判,而且是对理性形而上学本身的批判——在这里,“黑格尔哲学”所意指的不是形而上学之一种,而是形而上学之一切.这篇短文不可能就此提供哲学史上的论据,而只想简要地提示一点以表明它在哲学上的正确性.在马克思看来,“抽象物质”的观念具有和唯心主义同样的性质和方向(注: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这不过是因为对立的两极同样分享着理智形而上学的全部前提和预设.毫无疑问,在近代哲学的语境中,这种对立是有其充分而完整的意义的,因为近代哲学是整个地依赖于并通过这种对立而发展的.然而在当代哲学的语境中,上述对立恰恰是应当被更深刻地去理解和把握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证明,马克思是充分地达到了这一原则高度的;因为在他那里,旧唯物主义决不仅仅是与唯心主义对立的,毋宁说,“抽象物质”概念的真正意义倒是在黑格尔哲学中被完成和被揭示的.这样的意义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抽象的自然界”或“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亦即“物性”或“物相”;它和同源的作为纯粹活动的“自我意识”一样,乃是“脱离现实的精神和现实的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注: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8-120页;第129-131页.).就此而言,海德格尔的下述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把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倒转过来仍然还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x0d诚然,即使是费尔巴哈也已经意识到,“作为物性的物性”和“作为观念的观念”是同一种东西;但是,他试图用来遏制理性专制主义的“感性”原则却不但没有使他从形而上学中真正解脱出来,相反却导致了一种看起来是更加僵硬和无生气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它首先是并且应当被归结为本体论革命——正是由此处脱离,而不是于此处滞留.然而,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却远未得到充分的估价,那些对于此种本体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概念”——如“感性对象性”、“感性意识”、作为“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的“实践”、“劳动”、“人类社会”等等——也还未曾得到具有原则高度的澄清和阐明,甚至还没有在本体论方面真正被触及过呢.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由于使马克思哲学在本体论上滞留于费尔巴哈的那种境域,结果不仅极其严重地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而且为各式各样的曲解、无知和偏见大开方便之门.\x0d如果说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是最明确不过地把马克思的本体论局限于费尔巴哈的框架内,那么,他们所做的其他工作就是试图从黑格尔那里给上述框架作方法论上的补充.当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开始抨击“海林-普列汉诺夫正统”时,他的富有成果的努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他至少在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方面恢复了黑格尔对于费尔巴哈的优先权.至于这种解释的创意和局限,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来:一方面,虽然卢卡奇还主要是从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提出问题,但是在主体-客体的辩证法居于主导地位时,他便要求着使“主观性”或“主观方面”本质重要地进入到本体论的基础之中;但是另一方面,“黑格尔眼镜”使他无法从根本上真正克服那种保持在“同一”内部的对立,结果这种对立的再度活跃引导出来的乃是黑格尔哲学的“费希特因素”.无论如何,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卢卡奇之间,出现了一种有趣的但又意味深长的比照.我们仅举其中的一例:那个对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来说最为根本并且性命攸关的原则——“实践”,乃从分裂的和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去获得解释:当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实践”完全等同于费尔巴哈的“实践”(或“生活”)概念时(注:参见拙著《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关于“实践”概念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却以一种“夸张的高调”、以一种主观主义的“乌托邦主义”使实践概念“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从而在把“被赋予的意识”变为实践的同时,构成了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注: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13页.).\x0d不难看出,正是在这种对立中,马克思哲学(首先是其本体论基础)从根本上被分裂了;并且由于这种分裂,马克思在哲学本体论上的决定性革命和无与伦比的创制便隐遁了,或至少是暗淡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无论这两者之间是怎样的“比例”,无论这两者之间是如何地彼此斟酌损益,据说这就是马克思哲学.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根本谈不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如果说这种当代意义的遮蔽更加切近地是由于上面所提到的那种哲学基础的分裂,那么它同样还更加深刻地植根于生活世界本身的分裂之中.三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决不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好像它是可以现成地存在于某个地方似的(比如说,现成地居住在一套全集中).毋宁说,它倒是被发现的;正像此种意义只能历史地被遮蔽一样,它也必定只能是被历史地发现的.而意义生成的根本途径乃在于实际地形成“对话”.\x0d因此,在哲学范围内,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发现势必要求它与当代的哲学形成最广泛的和不断深入的对话.如果没有这种对话,它的那些被遮蔽的意义就不可能被再度揭示出来,而这些意义之最深刻的当代性也就不可能愈益透彻地得到领悟.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文化的真正核心,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如果它还在实际地领悟着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那就尤其正确.然而,对于这种当代性的切近领悟,只有在对话的途中才是真正可能的;反之,如果这样的判断只是激起了某种无责任能力而又自夸大狂的孤立主义,那么,领悟并揭示意义的辩证法也就终止了.\x0d伽达默尔在阐释20世纪的哲学基础时,完全正确地注意到马克思已经放弃了“黑格尔的概念立场”;但是,当他把马克思仅仅与弗洛伊德、狄尔泰和基尔凯郭尔并列起来作为本世纪的“出发点”,而使尼采作为“本世纪哲学运动的后盾”时,他却在哲学性质方面错估了马克思.“尼采是一个伟大的、预言性的人物,他从根本上改变了本世纪批判主观精神的任务”(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115页.).这一判断若就思想史上的影响而言,可以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当伽达默尔使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属于尼采的批判目标——意识本身的异化时,他却又一次在哲学性质方面错估了马克思.若就哲学性质而言,马克思不是尼采的一个特例,相反尼采倒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的一个特例——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从本质性方面着眼,那么我们有理由断言,尼采哲学之被发现了的意义使他成为当代哲学的天才预言家;而马克思哲学的伟大创制若进入到当代意义的光照之中,则远不止于“先知”,他还是本世纪哲学之最终结果的真正的“同时代人”.因为当尼采把关于主观精神的决定性追究给予当代从而使德国唯心主义的天真预设陷于虚假性时,他本身又回复到一种的虚假性之中;而马克思在初始是同一性质的批判中却走到了使任何一种r形而上学都无以规避的地步——当他一个接一个地击穿了全部旧哲学的那些“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和“概念的天真”之后,他的思想似乎是不可遏制地深入到当代哲学的真正核心中去了.我们希望很快能有机会为这一点提供详尽而充分的论证和阐述.\x0d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和尼采一样,对“绝对的形而上学”实施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性的“倒转”;然而由于这种倒转(仅仅是“倒转”),所以马克思又和尼采一样,重新转回到形而上学的另一种形式之中(注: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79页.).这样的判断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海氏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估价上:“与黑格尔相对立的马克思并不在自己把握自身的绝对精神中,而是在那生产着自身和生活资料的人类中看待现实性的本质.这一事实将马克思带到了离黑格尔最远的一个对立面中.但也恰恰是通过这样一个对立面,马克思仍然保持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里;因为,就每种生产的真正生产性是思想而言,现实性的生存总是作为辩证法、也就是作为思想的劳动过程而存在…….”(注:转引自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的附录,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46页.)如果说海氏对尼采的评估是卓越的,那么他使马克思与尼采相比附则是完全错误的;至于谈到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判断,那么与其说是错误的,毋宁说是幼稚的.这里确实牵扯到了问题的真正核心.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作为思想的劳动过程而存在”的生产性根本不意味着真正的劳动,相反倒是意味着“异化劳动”(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相一致);而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中所获致的作为“现实性的本质”的劳动,如果可以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表示的话,那么它在一方面意味着“此在”是“在世之在”(烦忙在世)(注: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7-73页.),在另一个方面则代表着“存在的真理”;并且正像海德格尔把“绝对的形而上学”归属于“存在的真理的历史”之中一样,马克思同样坚决地使“异化劳动”归属于这一历史.试问:这如何才是可能的?\x0d因此,全部问题在于,人们确实知道马克思对意识所作的本体论批判,但却并不真正理解这一批判的意义(当代意义),而对于该批判在本体论上作为积极成果而赢得的全新境域还几乎一无所知.海德格尔正是在这里错失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当他把马克思最终淹没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去之时,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敏锐洞察(注:海氏的说法是:“……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的意义也就变得极为有限了——这种意义仅仅局限在“历史的观点”或“历史学”之中.这种意义估价在性质上仍然十分类似于下述情况: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把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归并到费尔巴哈那里(甚至“机械唯物主义”那里(注:参见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99页.))去的时候,他们同样断言说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仅仅发生在“历史观”方面.试问:这种情况难道是可能的吗?\x0d在这里,我们当然无法就问题在理论上予以充分的展开,但我们有理由指出这样一点:当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在主要之点上被根本性地揭示的时候,上述问题中所蕴含的矛盾就应当而且能够被消除.不消说,在这种揭示使意义呈现的地方,原先被硬化的理论构造将整个地发生变化.例如,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当然将不再可能继续维持其作为外在方法论的那种形式,同样也不再可能如海德格尔所想象的那样作为“思想的劳动过程”而反过来巩固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但是作为一种现象实情,马克思的辩证法却使他完整地达到了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所达到的那个境域——至少就超越并终止一切形而上学这一点来说是如此.这种辩论法的真正性质实际上不可能仅仅通过赫拉克利特或黑格尔而得到完整的理解,它也许还应当通过当代哲学发展的某种迹象去领悟——伽达默尔曾多次提到海德格尔哲学的辩证法背景,而他自己则声言说,辩证法应当在解释学中得到复活.\x0d我们根本不想自诩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乃是在我们手中被现成地掌握着的东西;它从来就不是什么现成的东西,好像一个钱包可以丢失又被找回来一样.如果说这种意义从根本上来说乃是由历史所造成并且由历史不断地去造成,那么在哲学的范围内,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它只是在对话的途中生成并且呈现.在这样的意义上,若仅就代表性的标记来提示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要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真切意义,不能不读《存在与时间》,就像不能不读《精神现象学》一样.我们在这不想(也无权)就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作什么实质性的断言,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这一哲学真正地与当代思想形成批判性的对话时,它的当代意义不是被遮蔽而是被坚决地揭示出来;正像它在这样做时不是疏离了当代思想的任何一种积极成果,而是同样坚决地把它们据为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