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散文和读后感,随便一篇,最好是短一点的散文和读后感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7/27 23:1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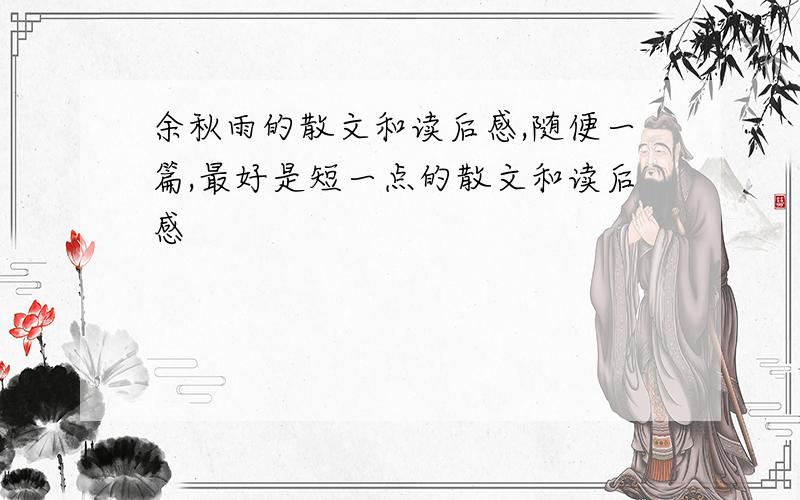
余秋雨的散文和读后感,随便一篇,最好是短一点的散文和读后感
余秋雨的散文和读后感,随便一篇,最好是短一点的散文和读后感
余秋雨的散文和读后感,随便一篇,最好是短一点的散文和读后感
读出了一种惋惜之情.文中的古屋听雨,是如何之诗意,如何之惬意啊.听、雨之纤纤细手拂弄着无数黑键啊灰键,把晌午奏成黄昏,听那点点滴滴点点,忐忐忑忑,忐忐忑忑,绵绵潇潇绵绵.一阵冷雨,把冬落成了春,把夏又拂成了秋.而如今之台湾,雨点却只能溶在水泥里,雨已成了没有音韵的乐音,瓦的歌唱已成绝响:雨来时,已不再,丛叶嘈嘈切切,不再闪动那湿湿的绿光,鸟声减了,蛙声沉了,虫吟没了.只是叹息,只是后悔,千片万片的瓦响已成了脑海中的一隅思念和回忆.这世间已再没有少年听雨,红烛成昏;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白头听雨,僧庐下了.
这种中国式的惋惜,是一种怀旧,是一种思念,是一种对祖国、对大陆、对家乡的思念.一位老人对大陆统一的期盼!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柜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磁石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下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沐浴之后特有的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和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住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安格罗萨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来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富云情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赖都歇的俱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气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上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问,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萦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像宋画,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亲,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再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更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在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据说住在竹楼里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是住在竹筒里,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黯,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黯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噬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幺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敲,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一夜盲奏,千层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持,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蝎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潮泻过,秋意便弥漫旧式的庭院了.
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吧那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咯咯,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胶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和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
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垂钓读后感
曾经读过余秋雨的许多散文,而让我时时不能忘怀的一篇就是《垂钓》了。《垂钓》是余秋雨夫妇在海参威的见闻,情节十分简单。一胖一瘦的两个垂钓老人,因为自己的喜恶,胖老人在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次下钩不到半分钟他就起竿,次次都会挂着六条小鱼,他忙忙碌碌地不断下钩、起钩,从来没有落空,落日余晖的时候,总是快乐地满载而归;瘦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钓钩只有一个,而且“硕大无比”...
全部展开
垂钓读后感
曾经读过余秋雨的许多散文,而让我时时不能忘怀的一篇就是《垂钓》了。《垂钓》是余秋雨夫妇在海参威的见闻,情节十分简单。一胖一瘦的两个垂钓老人,因为自己的喜恶,胖老人在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次下钩不到半分钟他就起竿,次次都会挂着六条小鱼,他忙忙碌碌地不断下钩、起钩,从来没有落空,落日余晖的时候,总是快乐地满载而归;瘦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钓钩只有一个,而且“硕大无比”,即使没有大鱼上钩,他都倔强地端坐着,等着“暮色苍茫”了,“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
两位老者不同的性格追求,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胖老人归去的时候已是盆满钵满,快乐的“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虽然“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薄”,但他毕竟鱼桶空空,一个人在暮色渐浓的大海边寂寞地等待,孤独地守候!
余秋雨在散文中说道“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美的人类”。的确,人类在演绎故事的时候,皆因为不同的人生观而丰富了结局,让旁观者更觉况味无穷。
也许有人认为胖老人是追求物质而胸无大志,随遇而安,浑浑噩噩地过着小鱼生活的现实主义者;瘦老人则是一个追求完美、志在高远、锲而不舍的理想主义者。然而,从生活的角度而言,我对胖老人的做法是报以赞许目光的。生活追求需要积极向上,却要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智慧,不容许有盲目和好高骛远的侥幸心理,胖老人十分明白自己所面临的客观条件,钩小滩浅,他不妒忌瘦老人钓钩的“硕大无比”,也不去打击他的执着,即使在“提起满满的鱼桶走了,快乐地朝我们扮了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怕的是惊扰了瘦老人的钓鱼梦,他的这份平常心,使得他非常快乐。也许,他一辈子都钓不上大鱼,但是在他面对的领域里,他,的确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优胜者。
瘦老人无疑是许多人认为的完美形象,他的身上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壮士之美。他的钓鱼钩“硕大无比”,可谓大矣,“在他眼里,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践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鄙视同伴的浅薄”,瘦老人是唯大鱼不钓的,他在浅浅的水域里等待大鱼上钩,俨然一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情形,他在苦作者:钱毅伟苦地单相思久久不愿上钩的大鱼之余,却没有实际地分析自己所处的客观条件,倘若他向大海深处更进十米、二十米,或许就有机会拥有胖老人意想不到的收获,“硕大无比”的钓钩上挂着他梦寐以求的大鱼儿。只是,他自视清高,鄙视胖老人的满载而归,却不曾想付出哪怕一点点智慧和艰辛!他的盲目执着在浅浅的沙滩边显得格外苍白,让观者体味到他的孤独和单薄。
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客观条件,一味盲目地追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目标,那种孤单寂寞的对峙并不能显示崇高,唯有不断地充实自己,发现自己,脚踏实地的面对和解决,才会象胖老人一样,面对人生自如地下钩、起钩,而且次次都是满满的六条活蹦乱跳的鱼儿,撞开人生的一扇扇希望和快乐之门!
垂钓(余秋雨)
去年夏天我与妻子买票参加了一个民间旅行团,从牡丹江出发,到俄罗斯的海参崴游玩。海参崴的主要魅力在于海,我们下榻的旅馆面对海,每天除了在阳台上看海,还要一次次下到海岸的最外沿,静静地看。海参崴的海与别处不同,深灰色的迷雾中透露出巨大的恐怖。我们眯缝着眼睛,把脖子缩进衣领,立即成了大自然凛冽威仪下的可怜虫。其实岂止我们,连海鸥也只在岸边盘旋,不敢远翔,四五条猎犬在沙滩上对着海浪狂叫,但才吠几声又缩脚逃回。逃回后又回头吠叫,呜呜的风声中永远夹带着这种凄惶的吠叫声,直到深更半夜。
在一个小小的弯角上,我们发现,端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垂钓的老人。
胖老人听见脚步声朝我们眨眼算是打了招呼,他回身举起钓竿把他的成果朝我们扬了一扬,原来他的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个钓钩上都是一条小鱼。他把六条小鱼摘下来放进身边的水桶里,然后再次下钩,半分钟不到他又起钩,又是六条挂在上面。就这样,他忙忙碌碌地下钩起钩,我妻子走近前去一看,水桶里已有半桶小鱼。
奇怪的是,只离他两米远的瘦老人却纹丝不动。为什么一条鱼也不上他的钩呢?正纳闷,水波轻轻一动,他缓缓起竿,没有鱼,但一看钓钩却硕大无比,原来他只想钓大鱼。在他眼中,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蹋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伟大的钓鱼者是安坐着与大海进行谈判的人类代表,而不是在等待对方琐碎的施舍。
胖老人每次起竿都要用眼角瞟一下瘦老人,好像在说:“你就这么熬下去吧,伟大的谈判者!”而瘦老人只以泥塑木雕般的安静来回答。
两个都在嘲讽对方,两个谁也不服谁。
过了不久,胖老人起身,提起满满的鱼桶走了,快乐地朝我们扮了一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发出,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仍在端坐着,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薄。暮色苍茫了,我们必须回去,走了一段路回身,看到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此时的海,已经更加狰狞昏暗。狗声越来越响,夜晚开始了。
妻子说:“我已经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胖,一个这么瘦了。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人世间的精神总是固执而瘦削的,对么?”
我说:“说得好。但也可以说,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类。”
确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没有瘦老人,胖老人的丰收何以证明?没有胖老人,瘦老人的固守有何意义?大海中多的是鱼,谁的丰收都不足挂齿;大海有漫长的历史,谁的固守都是一瞬间。因此,他们的价值都得有对手来证明。可以设想,哪一天,胖老人见不到瘦老人,或瘦老人见不到胖老人,将会何等惶恐。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对手也就是最大的朋友,很难分开。
两位老人身体都很好,我想此时此刻,他们一定还坐在海边,像两座恒久的雕塑,组成我们心中的海参崴。
雪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唏嘘的声音,像江浙一带下雪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的白色,也才是花一样的美丽。它好像比空气还轻,并不从半空里落下来,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然而它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黄昏时候的成群的蚊蚋(ruì),像春天酿蜜时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飞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着人身,或拥入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它静默无声。但在它飞舞的时候,我们似乎听见了千百万人马的呼号和脚步声,大海汹涌的波涛声,森林的狂吼声,有时又似乎听见了儿女的窃窃私语声,礼拜堂的平静的晚祷声,花园里的欢乐的鸟歌声……它所带来的是阴沉与严寒。但在它的飞舞的姿态中,我们看见了慈善的母亲,活泼的孩子,微笑的花儿,和暖的太阳,静默的晚霞……它没有气息。但当它扑到我们面上的时候,我们似乎闻到了旷野间鲜洁的空气的气息,山谷中幽雅的兰花的气息,花园里浓郁的玫瑰的气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气息……在白天,它做出千百种婀娜的姿态;夜间,它发出银色的光辉,照耀着我们行路的人,又在我们的玻璃窗上扎扎地绘就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和树木,斜的,直的,弯的,倒的。还有那河流,那天上的云…
<山居笔记> 酣睡在寒风中
“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记忆里晃动。
那时学校由造反派执掌,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体师生必须出操。其实当时学校早已停课,出完操后什么事也没有了,大家都作鸟兽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体验掌权威仪的唯一机会。
老师们都是惊弓之鸟,不能不去;像我们这批曾经对抗过造反派、现在已成瓮中鳖而家里又有很多麻烦事的学生也不能不去;只有几个自称“逍遥派”的同学坚持不出操,任凭高间喇叭千呼万唤依然蒙头睡觉。这很损造反派的脸面,于是在一次会上决定,明天早晨,把这几个人连床抬到操场上示众。
第二天果然照此办理,严冬清晨的操场上,呼呼拉拉的人群吃力地抬着几张耸着被窝的床出来了。造反派们一阵喧笑,出操的师生们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难道强迫这些“逍遥派”当众钻出被窝穿衣起床?如果这样做他们也太排场了,简直就像老爷一样。于是造反派头头下令,“就让他们这样躺着示众!”但蒙头大睡算什么示众呢?我们边上操边看着这些床,这边是凛冽的寒风,那边是温暖的被窝,真是让人羡慕死了。造反派头头似乎也觉得情景不对,只得再下一个命令:“示众结束,抬回去!”那些温暖的被窝又乐颠颠地被抬回去了。后来据抬的同学抱怨,这些被抬进抬出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从头至尾没有醒过。
由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众,只是发难者单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众者没有这种感觉,那很可能是一个享受。世间的惩罚可分直接伤害和名誉羞辱两种,对前者无可奈何,而对后者,地实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一个人要实现对另一个人的名誉羞辱,需要依赖许多复杂条件,当这些条件未能全然控制,就很难真正达到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常受围攻的人名誉未倒,而那些批判专家劳苦半辈子都未能为自己争来任何好名誉的原因了。
让他们站在寒风中慷慨激昂吧,我们自有温暖的被窝,乐得酣睡。抬来抬去,抬进抬出,辛苦了。
闲读梧桐 余秋雨
梧桐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前面,在花圃和草地的中央,在曲径通幽的那个拐弯口,整日整夜地与我们对视。
它要比别处的其他树大出许多,足有合抱之粗,如一位“伟丈夫”,向空中伸展;又像一位矜持的少女,繁茂的叶子如长发,披肩掩面,甚至遮住了整个身躯。我猜想,当初它的身边定然有许多的树苗和它并肩成长,后来,或许因为环境规划需要,被砍伐了;或许就是它本身的素质好,顽强地坚持下来。它从从容容地走过岁月的风雨,高大起来了。闲来临窗读树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某日,母亲从北方来信:寒潮来了,注意保暖御寒。入夜,便加了一床被子。果然,夜半有呼风啸雨紧叩窗棂。我从酣梦里惊醒,听到那冷雨滴落空阶如原始的打击乐。于是无眠,想起家信。想起母亲说起的家谱,想起外祖父风雨如晦的际遇。外祖父是地方上知名的教育家,一生两袖清风献给桑梓教育事业,放弃了几次外聘高就的机会。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他不愿屈从于非人的折磨,在一个冷雨的冬夜,饮恨自尽。我无缘见到他老人家,只是从小舅家读到一张黑色镜框里肃然的面容。我不敢说画师的技艺有多高,只是坚信那双眼睛是传了神的。每次站到它跟前,总有一种情思嬗传于我,冥冥之中,与我的心灵默默碰撞。
浮想联翩,伴以风雨大作,了无睡意,就独自披衣临窗。夜如墨染,顷刻间我也融入这浓稠的夜色中了。惊奇地发现,天边竟有几颗寒星眨巴着瞌睡的眼!先前原是错觉,根本就没有下雨,只有风,粗暴狂虐的北风。这时,最让我“心有戚戚”的便是不远处的那株梧桐了。只能依稀看到它黛青色的轮廓,承受着一份天边的苍凉。阵风过处,是叶叶枝枝互相簇拥颤起的呼号,时而像俄罗斯民谣,时而像若有若无的诗歌。不知怎的,外祖父的遗像又蓦然浮上眼帘,似与这株沉默的梧桐有种无法言喻的契合。不求巨臂擎天的闻达,但也有荫庇一方的坦荡。
次日醒来,红日满窗,竟是大晴。
惦念的是那一树黄叶。推开窗棂,读到的树,竟是一个显山露水的甲骨文字;没有昨日那遮天蔽日的叶子,剩下的是虬树挺干。我的心像是被谁搁上了一块沉重的冰,无法再幻作一只鸟,向那棵树飞去了。这一夜的风呵,就凋零了满树的生命!而风又奈你何,坠落的终要坠落,无须挽留,你还有一身傲骨与春天之前的整个冬季抗争!
于是,我读懂了梧桐的寂寞,不是慨叹韶华流逝的漠然,不是哀怨人潮人海中的孤寂,而是一种禅意,一种宁静和虚空的玄奥,服从自然又抗衡自然,洞悉自然又糊涂自然,任风雕雨蚀,四季轮回,日月如晦,花开花落,好一种从容淡泊的大度!不禁又感慨起外祖父的英年早逝,悲哀起他屈从天命的无奈、悲哀起那个年代里的人们。
又是一阵熟悉的树叶婆娑的沙沙声响,亲切地叩击着耳鼓。俯目望去,一个红衣女孩雀跃在那黄叶覆盖的小径,那模样似乎每一片叶子都在为她青春的步履伴奏。此刻,我的窗台上,扑进一阙蓬松的阳光,洒在案前昨夜未曾合上的一卷旧书上。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