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雾的精彩片段 ji a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11/30 06:48: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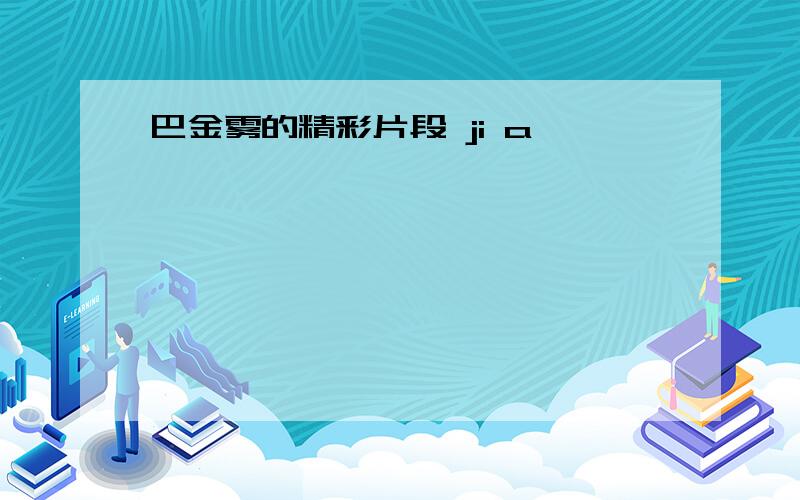
巴金雾的精彩片段 ji a
巴金雾的精彩片段 ji a
巴金雾的精彩片段 ji a
巴金《家》 31回 第二天早晨觉新到祖父的房里去请安,祖父得意地告诉他,冯家的亲事已经决定了,打算在两个月以后的某一天下定,叫他先去办理交换庚帖的事情.祖父还把历书翻给他看.他唯唯地答应着,退了出来,正遇见觉慧进去.觉慧望着他神秘地笑了笑.
觉新刚刚回到自己的房里,祖父又差钱嫂来叫他去.他进了祖父的书斋,看见祖父恼怒地责骂觉慧.祖父穿了一套白大绸的衫裤,坐在一把沙发上.陈姨太穿一件圆角宽袖滚边的浅色湖绉衫子,头发梳得光光,满脸脂粉,半边屁股坐在沙发的靠手上,正在给祖父捶背.觉慧一声不响地站在祖父面前.
“反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你去把老二给我找回来!”祖父看见觉新进来就沉下脸大声对他说,弄得觉新莫名其妙.
祖父说了话,又大声咳起嗽来.陈姨太加紧地给他捶背,一面尖声地劝道:“老太爷,你何苦这样动气.你看,你这样大的年纪,为着他们气坏自己身子也不值得!”
“他敢不听我的话?他敢反对我?”祖父喘了两口气,接着挣红脸断续地说:“他不高兴我给他定亲?那不行!你一定把他给我找回来,让我责罚他!”
觉新唯唯地应着,他已经明白一半了.
“这都是给洋学堂教坏了的.我原说不要把子弟送进洋学堂,你们总不听我的话.现在怎么样!连老二也学坏了,他居然造起反来了.……我说,从今以后,高家的子弟,不准再进洋学堂!听见了没有?”他说了又咳嗽.
“是,是,”觉新答应着,他惶恐地站在那里,祖父的每一句话打在他的头上,就像一个响雷.
觉慧站在觉新的旁边,他的心情却跟觉新的完全不同.他虽然感到空气压迫人,但是他并不惶恐.他一点也不害怕.他在心里暗笑,他想:“纸糊的灯笼快要戳穿了!”
祖父的咳嗽停止了,人显得很疲倦,便倒下去,渐渐地闭上了眼睛.陈姨太拿一把团扇轻轻地在他头上扇着,不让苍蝇钉在他的脸上.觉新弟兄依旧恭敬地站在他的面前,等候他的吩咐.后来陈姨太做了一个手势要他们出去,他们才轻脚轻手地走出了房间.
出了祖父的房间,觉慧第一个开口,他说:“大哥,二哥有一封信给你,到我屋里去看吧.”
“你对爷爷说了些什么话?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就跑去对他说?你真笨!”觉新抱怨觉慧道.
“笨?我正要叫爷爷知道!我要叫他知道我们是‘人’,我们并不是任人割宰的猪羊.”
觉新明白这些话是对他发的,他听起来有些刺耳,刺心,但是他也只好忍受.他说不出他的苦衷.他知道他纵然诚恳地向觉慧解释,觉慧也不会相信他.
他们两个人进了觉慧的房间,觉慧把觉民的信交给觉新,觉新几乎没有勇气读,但是终于读了:“大哥:我做了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人敢做的事情,我实行逃婚了.家里没有人关心我的前途,关心我的命运,所以我决定一个人走自己的路,我毅然这样做了.我要和旧势力奋斗到底.如果你们不打消那件亲事,我临死也不回来.现在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望你念及手足之情,给我帮一点忙.
觉民××日,夜三时.”
觉新读了信,脸色变白,手颤抖着,让信纸飘落在地上,口里喃喃地说:“叫我怎样办?”过后又说:“他太不谅解我了.”
“你究竟打算怎样办?现在不是谅解不谅解的问题,”觉慧严肃地说.
觉新好像受了惊似地突然站起来,短短地说:“我去把他找回来.”
“你找不到他,”觉慧冷笑道.
“找不到他?”觉新含糊地念着这句话.
“没有一个人晓得他的地址.”
“你一定晓得他的地址,你一定晓得!告诉我,他在哪儿?快告诉我!”觉新恳求道.
“我晓得,但是我决不告诉你!”觉慧坚决地答道.
“那么你不相信我?”觉新痛苦地说.
“相信你,又有什么用处!你的‘无抵抗主义’,你的‘作揖主义’只会把二哥断送掉.总之:你太懦弱了!”觉慧愤激地说,他在房里大步踱起来.
“我一定要去见他,你非告诉我他的地址不可.”
“我一定不说.”
“你将来总会说出来的,别人会要你说,爷爷会要你说!”
“我不说!在我们家里总不会有人拷打我,”觉慧昂然地说.这时候他只感到短时间的复仇的满足,他并没有想到别人的痛苦.
觉新绝望地走出去.不久他又走回来.他想找觉慧商量出一个具体的办法,却没有结果.他自己也想不出一个祖父同觉民两方面都能够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就在这天在周氏的房里开了一个小小的家庭会议,参加的人是周氏、觉新夫妇、淑华和觉慧.情形是这样:觉慧一个人站在一边,别的几个人又站在一边.大家一致地劝告觉慧说出觉民的地址,要他把觉民找回来.他们说了许多中听的话,甚至允许将来慢慢地设法取消这件亲事,但是觉慧完全拒绝了.
从觉慧这里既然得不到消息,而觉民的条件又无法接受,觉新和周氏两人也只有干着急.他们只得一面求助于克明,设法把交换庚帖的事情多拖延几天,不让老太爷知道;一面差人出去打听觉民的地址.
袁成和苏福甚至文德都出去打听过,可是并没有结果:觉民躲藏得很好,没有人知道他的地址.
克明把觉慧唤到他的书斋里正言教训了一番,没有用;温和地开导了一番,没有用;又雄辩地劝诱了一番,也没有用.觉慧老是推诿说他不知道.
周氏和觉新又拉住觉慧,央求他把觉民找回来,说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只要觉民先回家,然后慢慢地商量.觉慧却拿定了主意,在不曾得到可靠的保证之前,他决不把觉民找回家来.
周氏把觉慧骂了一阵,终于气哭了.她平日对待觉民弟兄虽然采取放任的态度,但是也关心他们的前途.现在情形严重,她不愿意看见不幸的结局,她更不愿意承担恶名.她不满意觉慧的目无尊长的态度,更不满意觉民的反抗家长、实行逃婚的手段,然而她始终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觉新处在这种困难的情形里,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他本来想承认觉民的举动是正当的,然而他无法帮忙觉民;他不但不能帮忙,反而不得不帮祖父压迫觉民,以致觉慧也把他当作了敌人.找不回觉民,无法应付祖父;找回觉民,又无以对觉民;而且事实上他又不能把觉民找回来.觉民是他的同胞兄弟,他也爱觉民,并且父亲临死时曾经把弟妹们交给他,要他代替父亲教养他们.现在觉民的事情弄成了这样,他怎么对得起父亲?他想到这里,只好躲在房里同瑞珏相对流泪.
这些事老太爷不会知道.他只知道他的命令应该遵守,他的面子应该顾全.至于别人的幸福,他是不会顾到的.他只知道向觉新要人.他时常发脾气,骂了觉新,骂了克明;连周氏也挨了他的骂.
然而骂也是没有用的,觉民丝毫没有屈服的表示.压力也无处使用,因为找不到人.事情传遍了全公馆.但是老太爷一再吩咐,不许传到外面去.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老太爷时时生气.觉新这一房的人都没有笑脸.别房的人大都幸灾乐祸地在暗中冷笑.
有一天觉慧刚在一个地方跟觉民秘密地会见以后回到家里,怀着一颗痛苦的心,别了那个绝望地苦斗着的哥哥,他好像别了整个光明的世界.家,在他看来只是一个沙漠,或者更可以说是旧势力的根据地,他的敌人的大本营.他回到这样的家里,马上就去找觉新,气冲冲地对觉新说:
“大哥,你究竟肯不肯给二哥帮忙?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
“我有什么办法呢?”觉新绝望地摊开手说.过后他心里想:“现在你倒着急了.”
“那么你就让事情这样拖下去吗?”
“拖!爷爷今天说再过半个月他不回家,就把他永远赶出去,并且登报声明他不是高家的子弟,”觉新苦恼地说.
“爷爷当真忍心这样做吗?”觉慧痛苦地叫起来,但是他并没有失掉勇气.
“有什么不忍心?现在正在他的气头上!……而且他打算跟二妹的亲事同时进行,同时下定.”
“二妹的亲事?爷爷把二妹许给什么人?”
“你还不晓得?她许给陈家了,不过还没有交换庚帖.就是陈克家的儿子.三爸自然赞成这门亲事,他跟陈克家本来很熟,他们又是同事.”
陈克家的名字觉慧太熟习了.陈克家大律师还是孔教会里的二等角色.谁都知道陈大胡子是悦来茶园二等旦角张小桃的相好.他常常带着张小桃进出他的律师事务所.他的“风流韵事”还多得很.觉慧气红了脸,大声骂起来:“陈大胡子的家里还出得了好人吗?我知道陈克家的儿子跟他父亲共同私通一个丫头,后来丫头有了孕才肯把她收房.”
“不,二妹是许给他兄弟的.关于丫头的事情,恐怕是外面的流言,不一定可靠.不过这跟我们并没有关系,横竖有别人作主.而且做媒的人就是冯乐山.”
“跟我们没有关系?你忍心让二妹嫁到那种人家去吗?这就是说又把一个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断送了.二妹自己一定不情愿!”觉慧愤怒地说.
“她不情愿又有什么办法?横竖有别人给她作主.”
“然而她是这样年轻,今年才十六岁啊!”
“今年十六,明年就是十七岁,也很可以出嫁了.你嫂嫂过门来,也只有十八岁啊!而且年纪轻,早早出嫁,将来倒可以免掉反抗的一着!”
“然而不征求她的同意,趁她年轻时候就糊里糊涂地把她的命运决定了,将来会使她抱憾终身的.他们就不想到这一点吗?这是多卑鄙的行为!”觉慧竟然骂起来.
“你为什么这样生气?”觉新痛苦地说,“他们只晓得他们的意志应当有人服从,所以你二哥的反抗也没有用.”
“没有用?你也这样说?怪不得你不肯帮助二哥!”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觉新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你不记得爹临死时是怎样把我们交给你的?你说你对得起爹吗?”觉慧愤怒地责备觉新道.
觉新不答话,他开始抽泣起来.
“我如果处在你的地位,我决不像你这样懦弱无用.我要自己作主,替二哥拒绝了冯家亲事.我一定要这样做!”
“那么爷爷呢?”过了许久,觉新才抬起头这样地说了一句.
“爷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难道你要二哥为了爷爷的成见牺牲吗?”
觉新又埋下头去,不作声.
“你真是个懦夫!”觉慧这样地骂了哥哥一句,就走开了.
觉慧去了,剩下觉新一个人在房里.房里显得十分孤寂,十分阴暗,空气沉重地向他压下来.他的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已经失了效力,它们没法再跟大家庭的现实调和了.他为了满足一切的人,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但是结果依旧不曾给他带来和平与安宁.他自愿地从父亲的肩头接过了担子,把扶助弟妹的事情作为自己的生活的目标,他愿意为他们牺牲一切.可是结果他赶走了一个弟弟,又被另一个弟弟骂为懦夫,他能够拿什么话安慰自己呢?在这样地思索了许久以后,他给觉民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信.在信里他把自己的心忠实地解剖了,他叙说了自己的困难的地位和悲哀,他叙说了他们兄弟间的友爱,最后他要求觉民看在亡故的父亲的面上,为了一家的安宁立刻回家来.
他找到觉慧,把信交给觉慧看,要觉慧给觉民送去.觉慧读着信,流了眼泪,默默地摇摇头,依旧把信装在封套里.
觉民的回信来了,当然是由觉慧带来的,信里有这样的话:“等了这许久,只得着你的这样一封信,老实说,我是多么地失望啊!……回来,回来,你反复地这样说.……我这时候坐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好像是一个逃狱的犯人,连动也不敢动,恐怕一动就会被捉回到死囚牢中去.死囚牢就是我的家庭,刽子手就是我的家族.我们家里的人联合起来要宰割我这个没有父母的孤儿.没有一个人肯顾念到我的幸福,也没有一个爱我的人.是的,你们希望我回来,我一回来你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们可以得到安宁了,你们又多看见一个牺牲品了.自然你们是很高兴的,可是从此我就会沉沦在苦海里了.……请你们绝了妄想吧,我的条件不接受,我是决不会回来的.在我们家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我带走了那么多的痛苦的回忆,这些回忆至今还使我心痛,它们常常压迫我,减少我前进的勇气.然而我有爱情来支持我.你也许会奇怪为什么我这次会有这样大的勇气.是的,连我自己以前也想不到.现在我有了爱情了.我明白我不仅为我自己奋斗,我是在为两个人的幸福奋斗,为了她的幸福我是要奋斗到底的.……大哥,你猜我这时候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家里的花园,想从前的游伴,我在想儿时的光阴.帮助我吧,看在父亲的面上,为了你做哥哥的情分.帮助我吧,即使不为着我,你也该为着她,为她的幸福着想,你也该给她帮忙.至少想着她的幸福,你也该感动吧.一个梅表姐已经够使人心酸了,希望你不要制造出第二个梅表姐来.……”
觉新的眼泪沿着面颊流下来,他自己并不觉得,他好像落在深渊里去了.四周全是黑暗,没有一线光明,也没有一线希望.他只是喃喃地说了两句:“他不谅解我,没有一个人谅解我.”
觉慧在旁边看着,又是气愤,又是怜惜.觉民的信他不但先看过,而且他还替觉民出主意写上了某一些话.他预料这封信一定会感动觉新,使他拿出勇气给觉民帮忙.然而如今他却听见这样的话.他想责备觉新,但是责备又有什么用处呢?觉新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人,而且已经没有自己的意志了.
“这个家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索性脱离了也好.”觉慧心里这样想.在这一刻他不仅对觉民的事情不悲观,而且他自己也有了另外的一种思想,这个思想现在才开始发芽,不过也许会生长得很快.
这些日子里,有好几个人为着觉民的事情在过痛苦的生活.觉民自己当然也不是例外.他住在同学黄存仁的家里,虽然黄存仁待他十分好,十分体贴,但是整天躲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行动不自由,不能做自己所想做的事,不能见自己所想见的人,永远被希望与恐惧折磨着,?这种逃亡的生活,的确也是很难堪的,而觉民又是一个没有这种经验的人.
觉民等待着,他整天在等待好消息.然而觉慧给他带来的却只有坏消息.希望一天比一天地黯淡,不过还没有完全断绝,所以他还有勇气忍受这一切.同时觉慧不断地拿最后胜利的话来鼓舞他.琴的爱情,琴的影像更给了他以莫大的力量.他终于支持下去了.他完全不曾想到屈服上面去.
这几天里面琴的确占据了他的整个脑子.他时时想念她,就在白天也做着梦,梦的尽是关于他和她的事情.希望愈黯淡,他便愈想念她;他愈想念她,便愈想见她.然而她那里他是不能去的,因为有姑母在家.他们两个人的住处虽然隔得近,却没有办法相见,而且连通信也不大方便.觉慧来看他的时候,他想写信给琴,托觉慧送去.可是一提起笔又觉得要说的话太多,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写起,又怕写得不详细反倒使她更着急.他决定找个机会跟她面谈一次.这个机会果然不久就来了,这是觉慧为他安排的.其实觉慧也并不曾费力,他知道姑母不在家,便把觉民带到琴那里去.
觉慧把觉民藏在门外,自己先进房去招呼了琴.他扬扬得意地对她说:“琴姐,我给你带了好东西来了.”
琴穿了一件白夏布短衫,手里拿着一本书,斜卧在床上,仿佛要睡去似的.她听见觉慧的声音,连忙坐起来,抛下书,理了理发鬓,没精打采地问一句:“什么好东西?”她的脸显得黄瘦了,眼皮又时时垂下来,好像一连几夜没有睡过一样.“你瘦了!”觉慧忘记回答她的话,却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
“你这几天也不来看我!”琴苦笑道.“二表哥的事情怎样了?为什么连信息也不给我一个?”她说着懒洋洋地站起来.
“几天?我前天不是来看过你吗?你看我今天到这儿来,汗都跑出来了.你还不谢我?”觉慧笑答道,他掏出手帕揩额上的汗珠.
琴在桌上拿了一把绘得有花卉的团扇递给觉慧,继续诉苦道:“你要知道我在这儿日子过得多长啊!快说,他的事情究竟怎样了?”她睁大了眼睛,眼里泄露出忧郁和焦虑.
“他屈服了,”觉慧进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说这句谎话,然而在这一刹那间一种欲望强烈地引诱他,使他不加思索地说出了这句来.
“他屈服了?”她痛苦地念着,然后坚决地说:“我不相信!”这句谎话在短时间内对她还不是一个厉害的打击.
她说得不错,因为这时候她的房间里突然出现了另一个青年.她的眼睛马上发亮了.她惊喜地叫了一声:“你!”这个“你”字所表示的究竟是疑问,是惊奇,是喜悦,是责备,她自己也没有时间去分辨.她几乎要扑过去.但是她突然站住了.她死命地望着他,她的眼睛里露出了许多意思.
“琴妹,当真是我,”觉民说,他真是悲喜交集,虽然还没有到流了泪又笑、笑了又流泪的程度.“我早就应该来看你,只是我害怕碰见姑妈,所以等到今天才来.”
“我晓得你会来的,我早晓得你会来的,”她欢喜地说,眼里不住地涌出泪来.她又用责备的眼光看觉慧,说:“三表弟,你骗我,我晓得你骗我.我相信他不会屈服,我相信他.”
“他是谁?谁是他?”觉慧的脸上浮出了善意的微笑,他找不到话答复她,便用这句旧话来嘲笑她.
她并不红脸.她骄傲地指着觉民说:“他就是他!”她露出满足的微笑.她用爱怜横溢的眼光看着觉民.
她的这个举动是觉慧不曾料到的,但是它给了他一个好印象.他笑了.他看觉民,觉民得意地立在那里自以为是一个英雄,因为受到了她的过分的称赞.
觉慧这时候才知道他先前的猜想是怎样地错误了.他以为这两个人的会面一定是很悲痛的,会有眼泪,会有哭声,会有一幕悲剧所应有的一切.因为在他们的家里这种事情是很寻常的.可是如今事实却跟他的猜想相反.这两个人是怎样地被爱情和信赖支持着,在那里面找到了希望和安慰,仿佛一切的阻碍都不能够分离他们.他们已经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了.没有悲痛,没有绝望,只有相互的信赖,足以蔑视一切的相互的信赖.在这一刻琴和觉民在他的眼前的确表演了这一幕爱情戏.这幕戏好像黑暗世界中的一线光明,给了他一个希望,他相信以后再用不着他的鼓舞,觉民一定不会屈服了.怀着热诚的青年就是如此容易相信人的!“好,不要再演戏了.你们有话还是赶快说吧,时间过得很快啊,”觉慧笑着对他们说;他又问:“可要我出去吗?”心里想:“总给我找到话来嘲笑你们了.”
他们对他笑了笑,并不去管他,也不回答他,就牵着手在床沿上坐下去,亲密地谈起来.觉慧便背转身在书桌上顺便拿起一本书来翻阅,这是《易卜生集》,里面有折痕,而且有些地方加了密圈.他注意地翻看,才知道琴这几天正在熟读《国民之敌》.他想她大概是在那里面寻找鼓舞和安慰吧.这样想着他不禁微笑了.他掉过头去看她.她正在跟觉民起劲地谈着,谈得很亲密,善意的微笑使她的脸变得更美丽,不再是先前那种憔悴的样子了.他不觉多看了她两眼,心里羡慕着哥哥.于是他回过头去,一边边?扇子,一边看书.《国民之敌》第一幕读完了,他又掉头去看她,她还在跟他说话.他读完第二幕又去看她,他们的话还没有完,他把全篇读完了再去看她,他们还是高兴地谈着.
“怎么样?这样多的话!”觉慧开始催促道.
琴抬起头看他一眼,笑了笑,又侧过脸去说话.
“二哥,走吧,你们已经谈得很够了,”过了半点钟,觉慧又在催促了.
觉民正要答话,却被琴抢着说了:“再等一会儿.时间还早,何必这样着急!”她紧紧地握着觉民的手,仿佛害怕觉民就要走开似的.
“我一定要回去了,”觉慧故意坚持说.
“好,就请你回去吧,我这个贱地方留不住你的贵脚,”琴赌气说.但是看见觉慧真要往外面走时,她和觉民又齐声把他唤住.
“三弟,你真要走?难道你连这一点忙也不肯帮我?”觉民诚恳地央求道.
觉慧笑道:
“我不过跟你们开玩笑,但是你们也太把我冷落了.琴姐,我来了这么久,你也不招呼我坐,也不跟我说话.你有了二哥就把我忘记了.”
两个人都笑了.琴笑着分辩道:“我只有一张嘴,我怎么能够同时跟两个人说话?三表弟,你听话些,今天让我跟二表哥多说些.你有话留到明天我们来说个够,”琴把觉慧当作孩子似地安慰道.
“不要这样骗我.我没有二哥那样的福气.”
“三弟,”觉民叫了一声,正要说下去,却被琴阻止了.琴抢着说:“你的嘴真厉害,我说不过你.我只问你喜不喜欢许倩如,她比我强多了,她才是一个新女子!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她的脸上露出狡猾的微笑.
“我也许喜欢她,也许不喜欢,这跟你有什么相干?也用不着你介绍,她又不是不认得我,”觉慧调皮地说,他对这种争辩感到了大的兴趣.
“你说得不错,我是这样想.他们两个思想都很新,都很激烈,”琴还没有答话,觉民却好像记起了什么似的,带笑地向着琴点头,表示赞同她的意见.
觉慧自然明白他们的意思,笑着挥了挥手说:“我不要学你们的榜样,我不会演戏.”他掉开头,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要的就是你!”但是第二个念头又马上跑来把第一个念头赶走了.这个念头是:“我已经断送了一个少女的性命,我不再需要爱情了.”他只是笑着,只是苦笑着.
琴和觉民的谈话终于到了完结的时候.现在他们不得不分别了.觉民实在不愿意离开这个房间.他觉得不仅是她,甚至这间屋里的一切对他都是十分宝贵的.他踌躇了.他望着她,他又想到那个小房间,那种孤寂的、等待的生活,他没有回到那里去的勇气.然而觉慧立在他的旁边.觉慧的催促的眼光提醒了他,他明白自己必须回到那里去.此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好像预料到就要从光辉的天空坠入黑暗的深渊里去似的,他绝望地、悲伤地、而且多少带了一点挣扎地说:“我去了.”可是他一时却拔不动脚.他还想说几句话安慰她,然而仓卒间找不到适当的话,他却说了一句“你不要想我”.他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他正要她时时想念他.
琴立在觉民的面前,两只大眼睛水汪汪地望着他.她很注意地听他讲话,好像预料到他有什么不寻常的话对她说.然而他却没有.她等了许久,他只说了短短的两句.她失望了,她害怕他马上就走开.她连忙挽留道:“不要就走,等一会儿,我还有话对你说.”她拉住他的袖子.
他吞了这些话好像吞下好的饮食.他呆呆地望着她的激动的脸,他的眼光透过眼镜片看入她的眼里.他的嘴唇迟缓地动着,他带着微笑说了下面的话:“不要急,我不会走.”他的笑脸跟哭脸差不多,觉慧在旁边以为他真的哭了.
琴觉得觉民的温柔的眼光在爱抚她的眼睛和她的脸,好像在说:“你说呀,你说呀!你所说的,无论是一个字或一句话,我都注意地听着.”她想找些可以永久安慰他、使他永远不会忘记的话来说,然而她找不到一句值得他听的话.她望着他,她着急.她害怕他就会转身走了.她依旧拉住他的袖子不放.她不再选择话了.她想到什么,立刻就说出来,并不去考虑这些话有没有说的必要,或者跟他有没有关系.
“倩如来说,我们学堂里头的文和‘老密斯’要到北京读书去了.她们在这个环境里实在忍受不下去.她们的家庭也怪她们不该剪头发,”琴开始说,她并不向觉民解释文和“老密斯”是什么人,好像他已经熟识了这些名字和绰号.然而觉民却很注意地听着,仿佛感到大的兴趣似的.
“倩如自己恐怕也要走.她父亲因为她的事情受到了攻击,他很愤慨,说是要把交涉署的职务辞掉,带了女儿搬到上海或者南京去住.”这也是琴的话,觉民依旧很注意地听了.
“梅姐近来病得厉害.她天天在吐血,不过吐得也并不多.她瞒着她母亲,她一定不要我告诉人,她不愿意吃药.她说她多活一天只是多受一天的罪,倒不如早死了好.她母亲整天忙着拜客、打牌,不大管她.倒是大表嫂常常想着她,给她送药,送东西去.我昨天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把她的病状告诉她母亲了.她母亲才着急起来.梅姐的话也许是对的,不过我不能够看着她死.你们不要告诉大表哥.她嘱咐我千万不要让大表哥知道她吐血的事.”这也是琴的话.她忽然发见觉民的眼睛被泪水充满了,泪珠开始在眼镜片后面沿着面颊流下来.他的嘴唇微微动着,好像再说什么话,却说不出口.不过她已经懂得了.她还想说什么,但是一阵无名的悲哀突然袭击了她,很快地就把她征服了.她说了一两个字,又咽住了.她在挣扎,她终于迸出了一声哭叫:“我不能够再说下去了!”于是向后退了几步,用手蒙着脸,让眼泪畅快地流出来.
“琴妹,我去了,”觉民悲声说,他实在不愿意走,然而到了这个时候他也只得走了.他料不到他们这次的快乐的会面会以伤心的哭来结束.可是两个人都哭了.许多的话,许多的事,都以哭来了结了,不管他们怎样自命为新的青年,勇敢的青年.
“不要去!不要去!”琴取下她的遮住脸的手,向觉民伸过去,悲声叫道.
觉民正要向她扑过去,他的膀子被觉慧抓住了.他便站住,默默地掉头去看觉慧.觉慧并没有哭,干燥的眼里发出强烈的光.觉慧把脸向后面一掉,是叫他走的意思.他觉得觉慧的意思不错.他转过头用他的悲痛的声音安慰琴:“琴妹,不要哭,我会再来的,我们的住处隔得这么近,有机会我一定来看你.……我回去了,你好好保重,等候我的好消息.”他把心一横就跟着觉慧走了出来,留下琴一个人在那间开始阴暗的屋子里.
琴看见他们走了,便追出去,到了堂屋门口,她站住了,身子靠在门框上,注意地望着他们的背影.
01章
夜来了,这是海滨的一个静寂的夏夜。
海水静静地睡着,只有些微的鼾声打破了夜的单调。灯塔里的微光在黑暗的水面上轻轻地颤抖,显得太没有力量了。
离海有里多路远,便是荒凉的街市。在夜晚街上更静了。
虽然是在夏天,但这里的夜晚从来就很凉爽:海风微微吹着,把日间的热气都驱散了,让那些白日里忙碌奔波的人安静地睡下来。也有人不忍辜负这凉爽的夜,便...
全部展开
01章
夜来了,这是海滨的一个静寂的夏夜。
海水静静地睡着,只有些微的鼾声打破了夜的单调。灯塔里的微光在黑暗的水面上轻轻地颤抖,显得太没有力量了。
离海有里多路远,便是荒凉的街市。在夜晚街上更静了。
虽然是在夏天,但这里的夜晚从来就很凉爽:海风微微吹着,把日间的热气都驱散了,让那些白日里忙碌奔波的人安静地睡下来。也有人不忍辜负这凉爽的夜,便把椅子摆在门前,和邻居们闲谈他们生活里的种种事情,而最引起他们注意的便是那所新式建筑的海滨旅馆。
这四层的洋楼孤零零的高耸在那些邻近的简陋的矮屋上面,显然是位置在不适宜的地方。它骄傲地俯瞰着那些矮屋,而且以它的富丽的装饰、阔绰的住客和屋前的花园向它们夸耀。
在夜里和在白昼一样,这旅馆和那些矮屋依然形成了两个阶级,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在旅馆里灯烛辉煌,人们往来,似乎比在白昼更活动了。
一辆汽车在旅馆的大门前停住,司机下来开了门。一个瘦长的青年弯着身子从车里出来,带着好奇的眼光向四处看,似乎有点奇怪:这样的旅馆竟然安置在如此荒凉的街市中间。
从旅馆里走出来两个侍役,都带着恭敬的笑容,一个从司机手里接了那两件并不很重的行李,另一个引着青年走过微微润湿的草地,向里面走去。
那青年踏上了石阶,昂然走进门去。他走了不到几步便看见一个年轻女子从楼梯上下来,穿的是白夏布衫和青色裙子。她有一张丰腴的脸,白中透红的皮肤,略略高的鼻子,和一对星一般明亮的眼睛,左眼角下嵌着一颗小小的黑痣,嘴边露着微笑。
他望着她,呆了一下,就惊喜地叫起来:“密斯张。”
她马上转过身子惊讶地望了望他。她忽然微微张开嘴,嘴唇皮一动,微笑了。于是她迎着他走来,两颗漆黑的眼珠发光地看着他,问道:“周先生吗?几时回来的?”
“快一个星期了,”他愉快地答道。“我去看过剑虹,说我要到这里来小住一些时候。他说密斯张也在这里,要我来看看你,想不到一到这里就遇见了。真巧得很。”
“是的,真巧。我也想不到周先生会到这里来。剑虹先生前两天有信来也不曾提到周先生回国,所以我不知道。”她歇了歇,不停地用她那对明亮的眼睛看他,态度很大方。他还来不及想到适当的话,她又接着说下去:“我打算在这里住过这个暑假,顺便温习功课。今年我不回家。一个人住在这里虽然清静,只是读书没有人指导也不方便。现在周先生住在这里,我倒可以常常向周先生请教了。”她的脸上笼罩着一道喜悦的光。她显然很高兴这次意外的会面。她的家就在邻近的一个城市里,搭小火轮去只有一天的路程。所以她说了今年不回家的话。
“密斯张,你太客气了,我哪里配说指教人?我们在一起研究就是了,”他谦逊地说着,心里也很高兴。
“我说的是真话,倒是周先生太客气了。以后请教的地方多着呢。”她还想说下去,忽然瞥见那两个侍役,一个提了行李,一个垂着双手,都恭敬地立在旁边带笑地看他们两个说话,她便说:“周先生住几号房间?我现在不打扰周先生了。
……我就住在二楼十九号,周先生有空请来玩。”她向他点了点头,并不等他回答,就走进旁边一间题着“阅报室”的屋子去了。
这里周如水也对她点了点头,带笑说,“等一会儿把房间弄好,我就过来看密斯张,”于是跟着侍役上了楼。
侍役们在三层楼上一个房间的门前站住了。空手的侍役掏出钥匙开了门让周如水进去,接着另一个侍役也提着箱子进来。
“就是这个房间,周先生中意吗?”空手的侍役这样说了,接着又说一些形容这房间的优点的话,便抬起脸恭敬地静候着他的回答。
周如水向四面看了一下,觉得这房间大小还中意,陈设也过得去,便点头答道:“还可以。”他看见窗户大开着,便走到窗前。他从窗户望外面,远远地是一片黑暗的水,一线灯光在水面荡漾。凉爽的夜气迎面扑来,他觉得十分爽快,抬起头去望天空,满天的星斗对着他在摇晃。他又把头埋下去,从各个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正照在草地和矮树上。
作者: Aijay辛依 2005-3-7 09:25 回复此发言
--------------------------------------------------------------------------------
2 《雾》《雨》《电》之《雾》(连载)
“这里很不错。”他回过头来向侍役称赞了一句,又问:“这是多少号房间?”
“三十二号,”侍役得意地答道。那个提行李的侍役已经走出去了。
“周先生没有用过晚饭吗?”侍役又问。
“吃过了。你给我弄点茶来吧,”周如水说着,就脱下他的太阳呢西装上衣挂到衣架上去。
侍役答应了一个“是”字,往外面走了。
房里剩下周如水一个人。他望着五十支烛光的电灯泡,慢慢地嘘了一口气,又把眼光移去看那个画得有花卉的方灯罩。
于是他在那把有白布套的躺椅上坐下去,庆幸似地自语道:“在这里该可以有一些时候的安宁了。我一定要有一点好的东西写出来才好。”他微笑地闭上眼睛来体会这安静的快乐,可是白衣青裙的影子却突然闯进他的眼帘来。
一年前的印象浮上了他的脑海。那时他刚从日本回来,在他所尊敬的前辈友人李剑虹的家里遇见了一个使人一见就起新鲜感觉的女郎。这白衣青裙的装束,虽然很朴素,却有着超过那班艳装女子的吸引力。她那双明亮的眼睛照亮了她的整个安排得很适当的脸庞。同时她的一举一动都保留着少女的矜持和骄傲。近几年来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某些日本女子的面影:那些柔媚得好像没有骨头、娇艳得好像没有灵魂的女性,他看得够多了。出乎意外的,他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少女。
于是他带着好奇的、景慕的、喜悦的感情和她谈了一些话。她的思想又是那么高尚,使他十分佩服。他们分别的时候,她和他只见过两三面,而她的姓名就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脑子里了,这是三个美丽的字:张若兰。
以后在东京的一年中间他并没有忘记这个美丽的名字。
他常常想起她那明眸皓齿的面庞,就仿佛在黑暗里看见一线光亮。他好几次想写信给她,而且已经开始写了,但终于不曾写好一封。她也没有信来。他很想知道她的消息,他鼓起了绝大的勇气,才在给李剑虹的信里,附加了一句,问到她的近况。那个前辈的友人似乎不知道他的心理,虽然在回信里把她赞扬了一番,却把她形容为一个高不可攀的女子。这反而把他的勇气赶走了。他以后也就不曾再提起这个名字。
但是如今他却在这里见着了她,而且是同她住在一个旅馆里。以后他每天都有机会看见她,她还说过求他指教的话。
他这样想着,他觉得快乐从心底升起来,渐渐地在膨胀,使得他全身因发热而颤抖了。他静静地在躺椅上坐了一些时候。后来他实在忍耐不住,便站起来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忽然急急走出房门,往二楼去了。
他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十九号房间。他站在房门前,迟疑了一些时候,才把两根指头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房里的脚步声响了。他连忙往后退一步。房门打开,她出现了,蒙着淡淡的绿光,她的整个身子带着一种异样的美,两只晶莹的眼睛射出喜悦的光。
“请进来吧,”她笑着说,微露出一排白玉似的牙齿。她退后一步,身子往旁边一侧,让他走进房去。
一盏绿色灯罩的桌灯放在小小的写字台上,桌子前面有一把活动椅。周如水在椅子上坐下以后,略一掉头,就瞥见摊在桌上的十六开本的《妇女杂志》,是新出的一期,上面发表了他写的两篇童话,而且编者在《编辑余谈》中还写了过分推崇的语句,说他是留日的童话专家。现在他在她的写字台上看见这本杂志,觉得她已经读了自己的文章,并且加以赞美了,于是他的脸上浮出得意的微笑,他不觉把杂志接连看了几眼。
她好像知道他的心理似的,马上笑着说:“周先生的文章已经读过了。在报上看见广告,知道有周先生的文章,所以特地买来拜读。周先生的文章真好。”
他听了这样的赞语,心里虽然很高兴,脸上却做出不敢承受的样子,连忙谦虚地说:“不见得吧。不过是一时胡乱写成的,真值不得密斯张一读。”同时他却暗地责备自己为什么写得那样慢,不曾多写几篇出来。他这样想着,他的脑子里浮出了新近写成的一篇短文的大意,觉得如果把这个意思向她表白,她也许会更了解他,更赞美他吧。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