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西方文论的相关内容,论述文学艺术的社会启蒙功能四百字左右采纳后会加赠20分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11/16 14:5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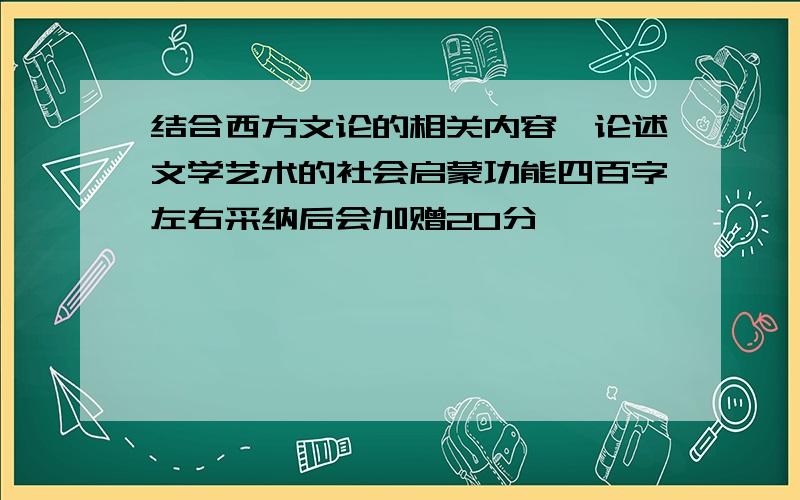
结合西方文论的相关内容,论述文学艺术的社会启蒙功能四百字左右采纳后会加赠20分
结合西方文论的相关内容,论述文学艺术的社会启蒙功能
四百字左右
采纳后会加赠20分
结合西方文论的相关内容,论述文学艺术的社会启蒙功能四百字左右采纳后会加赠20分
启蒙时代文论的哲学基础
一、从“经验理性”回到“怀疑”
要进一步读解18世纪启蒙主义文论,首先应当建立的问题意识必然关系到“理性”对17世纪与18世纪欧洲人的不同涵义.即:作为同样崇尚理性的思想者,18世纪代表人物所说的“理性”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理性的世界观为现代西方文论提供了什么样的背景?“经验的理性”在何种意义上进一步张扬了个人的自主性,乃至成为当代人批判“现代性”和“主观主义的客观主义”之主要标靶?
Richard Tarnas 《西方心灵的激情》(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一书提到:“启蒙运动是从一种史无前例的、对人类理性的确信开始的.科学在解释自然界方面取得的成功,以两种方式影响了哲学的进路:(1)把人类知识的基础植根于心灵及其与物质世界的接触;(2)把哲学引向对人类心灵的分析.”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对应、以及对主体心理的关注,其实也正是启蒙主义之后的西方文论重心.其基础被认为是17世纪末期英国哲学家洛克及其《人类理解论》(1690).
洛克与笛卡儿侧重“内在性”的理性分析完全不同,试图将17世纪对“内在观念”的理性主义信仰、转换为一种经验主义的原则.——“在人的理智中,没有任何东西未曾在感觉中存在过,……心灵如一块白版,经验在其上写下东西,从而心灵才取得合理的结论”;因此人类心灵中的“力量”是内在的,心灵中的“观念”却不是内在的,而是随“感觉”展开的“认识”.
洛克的理论通过伏尔泰传到欧洲大陆,结果是引起了对于“理性绝对主义”的更大怀疑.人们感到:即使是“科学”也只能在“有关现象的假设之基础上”发现“或然的真理”,而并不能揭示事物的真实结构.这样,“理性”的种种假设、甚至理性本身,都随之动摇.可以从洛克到贝克莱《人类认识的原理》(1710)、休谟《人类悟性研究》(1748)看到一条有趣的线索.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洛克不得不对“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加以区分.前者是物体自身的性质(如重量、形状),或可称“对象”;后者是人对物体的主观经验(如色、香、味),亦即“印象”.正是由于这样的“质”是确定的,所以人类的科学认识才成为可能,科学认识的结论才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也许在洛克看来,通过这一区分,“经验理性”的基础就可以更加稳固、“经验理性”的认识就可以免遭怀疑.但是贝克莱并不相信这一点,并且尖锐地指出了洛克的漏洞.
贝克莱认为:无论“第一性的质”还是“第二性的质”,实际上都是人类心灵对于“质”的感觉,所以它们最终的体现不过是心灵当中的“观念”.而“观念”是否能真正代表它所表达的物质对象、甚至是否能真正相似于该对象,在“经验理性”中都不可能有最后的定论.那么进而言之,与这些“观念”相对应的物质世界是否真正存在,也是无法肯定的.这就是说:“经验”只能形成“观念”、而不能证明“实在”;如果不能在“经验”之外找到其他正当的基础,人类的一切经验性认识就仅仅是心灵化的,却并不一定反映了客观的现实.这样,通过“经验”所了解的世界,其实不过是证据不足的假设.洛克试图从“经验”为理性认识提供辩护理由,结果却被贝克莱用“经验”消解掉了.
不过作为一位主教,贝克莱更需要从“经验”走向信仰、而不是彻底的怀疑.所以他最终要论证的,是个别心灵之上的“普遍心灵”——即上帝.上帝一旦存在,人类的经验就可以不断去体会上帝所揭示的奥秘;如果这“奥秘”被视为“自然的定律”,那么理性的科学仍然是可能的.在这里,经验性认识的物质基础虽被质疑,毕竟还留下一重信仰的基础,从而对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批判而言,贝克莱的怀疑还远非极致.于是随着经验理性的层层展开,休谟必然要出现.
休谟的起始性论题是对“印象”与“观念”的区分.这恰好处于洛克和贝克莱之间:他必须越过洛克的“对象”,因为那已被贝克莱证明为“观念”;他也必须又撇开贝克莱的“观念”,因为它所归属的上帝仍然是“经验的理性”无法证实的.这样,感觉印象被确定为认识的基础.这一出发点似乎比贝克莱更加“经验”,但是它对“经验理性”和“既有真理”的否定却是毁灭性的.
根据休谟的论证,“感觉印象”是个别、散乱的;之所以可以从“感觉印象”达成被人类假定为“真理”的知识,仅仅是因为我们在“感觉印象”之上强加了心灵自身的秩序.这“秩序”就是“一切人类认识的假定基础”——因果关系.而问题在于:“因果关系”只能在表面上得到经验的肯定,就较为严格的意义而言,它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真正得到直接的经验证实.人们所谓的“因果关系”,其实是来自多次重复、却并未穷尽的经验积累,所以只能被视为一种对预期结果的揣测和心理期待.
在怀疑情绪日趋普遍的20世纪,休谟的论题或许已不会耸人听闻,但是对于正处在“理性独断主义迷梦”之中的人们,休谟的怀疑确实相当可怕.“理性的推论”被他动摇了,任何有所“期待”的推论都不能自称与世界真相存在着必然联系;“理性的归纳”也被他动摇了,因为支撑着“归纳”的只是对个别例证的“揣测”.如果连“经验理性”的“归纳”也不能得到逻辑上的合法性,那么人类所渴望的任何真理或确定知识,便完全失去了可能.最为有趣的是:以休谟等人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批判,本来似乎是要将已经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获得成功的“经验”方法推广到“人”的研究领域,结果却是在不断推翻经验科学的客观确定性.
上述思路中的休谟,要比洛克和贝克莱彻底得多.对于他,所有规律、真理、实体、甚至上帝,都是理性所虚构的信念,而绝不是必然的.对于他,“真理的标准”一旦从“理念”转移到“经验”,便也意味着真理内容的彻底相对化、或然化.在休谟之后,西方人曾经拥有的一切“真理”,都不得不面临重新的检点.20世纪以来“怀疑”和“否定”的普遍情绪,正是以此为枢纽.
二、从“理性的设定”到“合理化”
就正面的价值而论,宗教改革以后真正为近代西方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被认为是“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如:斯宾诺莎(《伦理学》)、霍布斯(《利维坦》)、洛克(《人类理解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等.这正是启蒙主义文论的哲学基础,
所谓“自然法”其实就是“理性”.按照自然法学派的看法,人类的自然状态、自然处境和自然权利是一种相互关联的逻辑前提;同样基于这种逻辑前提的不同个人,要在群体中与他人相处,便会通过相互制约达成一定的理性约束;这种理性的约束就是人与人的“契约”,就是“自然的律法”,也就是一切传统、道德、社会制度的基础.在这一逻辑线索中,自然状态的“个人”是一切法理的出发点;作为自然律法的“社会契约”,是理性的对象化结果;从而“个人”的独立价值可以与“理性”的要求相互说明.
关于“个人”的逻辑预设显然并没有充分的根据,因此“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对于个人的界说有时甚至完全相反.霍布斯将人的自然状态设想为相互敌对;洛克则认为自然的人应当是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自然法学派”作为一个思想的整体,也许只是在一个基本问题上相互呼应,即:人类从自然状态向“公民社会”的发展,必须取道于理性的社会契约.
霍布斯:“自然律是理性所发现的……一般法则”,它“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生命或者剥夺自己生命手段的事情,并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情”.
洛克:“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的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人生、健康、自由或者财产.”
这实际上是说:基于自然状态的人,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和利益的稳定性,必然会合乎理性地与他人达成利益的平衡和相互的妥协,所以每一个个人都参与了社会契约的缔结,所谓国家也就是每一个个人相互结成的理性共同体.
“自然法学派”的这些思想,显然是力图更加贴近古代式的“和谐”乃至卢梭《社会契约论》所表达的某些理性,竟与黑格尔对古希腊社会的描述如出一辙:“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从这一意义上看,卢梭所谓的“回到自然”也就是回到理想中的古代“和谐”.
但是问题在于:这种从“个人”出发的“理性”,最终是通过“个人”与“理性”的统一,达成“个人与社会之间相对合理化的互制”.而在启蒙理性背景下的“合理化”,往往并不是自我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古代式“和谐”,却是重新成为外在权威、成为“环境”对“人”的规定性.
也许就是因此,启蒙主义时代的文论在经验理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种对于“环境”因素的特别关注.在这条线索上,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已经从方法论(培根)、认识论(洛克)、伦理学与政治学(霍布斯)方面对“环境”加以强调;法国人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以及所谓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孟德斯鸠).
具体到当时最为典型的文论思想,除去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对古希腊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分析之外,狄德罗、莱辛也都提出过相似的“情境说”.